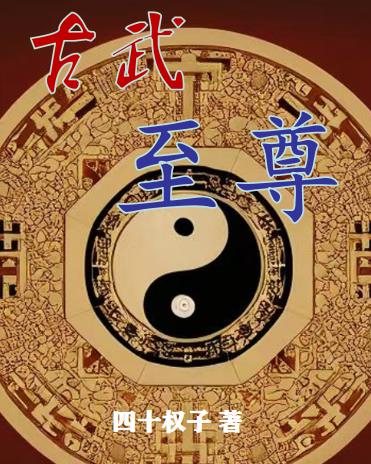安德列耶夫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h3>——一部找到的残稿</h3><h3>第一部分</h3>
<strong>片断一</strong>
……疯狂和恐惧。
我们顺着一条大道走去,这时我头一次感觉到了这一点——十个小时了,我们不间断、不停留地走着,不放慢速度,也不把倒下的人扶起来,而是把他们留给了敌人;大批的敌人正密密麻麻地在我们后面移动,三四个小时后他们便把我们的足迹踩平了。是个大热天。我不知道温度有多高:四十度,五十度,或许更高。我只知道那是一种持续的高温天气,热得厉害,密不透风。令人绝望。太阳是那么大,那么火烈烈地可怕,仿佛地面已经离得它很近,很快将被这团无情的烈火燃烧殆尽。眼睛都不看东西了。缩成很小的,小得像罂粟花籽的瞳孔,在合起的眼睫毛庇护下白白地寻找阴凉:太阳穿过薄薄的表皮,把自己鲜红的亮光刺进极度疲惫的脑子里。不过,毕竟这样要好些,所以我久久地,也许是几个小时地闭着眼睛走着,边走边听自己周围的人群怎么在行动:人们的一双脚和马儿的四个蹄子沉重而不平稳的步伐,铁轮子压在碎石子上发出的吱吱咯咯声,以及有人艰难疲惫的呼吸和干瘪的嘴唇的咂巴声。不过,我没有听到有人说话。大家都沉默不语,好像是一支哑巴的队伍在行军,如果有谁跌倒了,也是默默地倒下去,然后被别人踩到了才默默地站起来,也不看看四周围,继续朝前走——这些哑巴都是既聋又瞎的人。我自己就几次踩着人跌倒了,于是不由自主地睁开了双眼——而我看到的,真好像是失去理智的大地的一种荒唐的构想和沉重的梦呓。炽热的空气在颤抖,而且连石头也无声无息地在颤抖,仿佛要流动起来似的;而在拐弯处,一队队远去的人们、大炮和马匹,则仿佛脱离了地面,无声而僵硬地在摇晃——好像在行走的不是些活人,而是一支支无形的影子的大军。一个巨大的、离得近近的可怕的太阳,在每一支枪管、每一块金属号牌上都点燃了数千个令人目眩的小太阳,而且它们从四处、从两侧和下面钻进眼睛里,炽热尖利得像白光闪闪的刺刀尖端。燃烧般令人难受的炎热直达身体的最里边,进入骨头和脑子,于是有时感到奇怪,在肩膀上摇动的仿佛不是脑袋,而是个什么古怪和不寻常的球,它笨重而又轻巧,陌生并令人害怕。
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家:房间里的一角,一小片浅蓝色的壁纸,还有我小桌子上放着的一个长颈玻璃瓶,那里边装着水;因为没有人用它,外面落满了灰尘;我的那张小桌子,一条腿比另外两条短些,所以底下垫着一块叠起来的纸头。我的妻子和儿子好像在隔壁一个房间里,所以我现在没有看到他们。如果我能叫喊,我就要叫喊起来了——这种普通而和平的情景,这小片浅蓝色的壁纸和那没有人用而落满灰尘的长颈玻璃瓶,是那么平平常常。
我知道自己举着双手停了下来,但是有谁从后面推了我一把;我于是很快地大步向前扒开人群,急忙向什么地方走去,已经既不觉得热也不觉得累了。我像在无穷无尽的默默的队伍中穿行了好久,绕过被晒红的后脑壳,几乎碰着倒悬着的热乎乎的枪刺,这时一个想法使我停下来了——自己这是在干什么,这么慌慌忙忙要往哪里去。我还同样慌忙地向一边转过身去,穿过一片开阔地带,爬过一道沟谷,忧心忡忡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仿佛这块毛糙的热乎乎的石头就是自己全部努力的目标。
而这时,我头一次感觉到了这一点。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人,这些在太阳的闪光下默默地迈步走着的人,这些累得和热得要死、摇摇晃晃和正在倒下的人——全都发了疯。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太阳,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长在他们脖子上的,不是脑袋,而是些古怪而可怕的球。瞧这一个,他和我一样,正匆匆忙忙地穿过队伍并在跌倒;瞧另一个、第三个。瞧一匹马的头部伸到了人群的上边,它长着两只疯狂的眼睛和一张龇着牙齿张开着的正要发出某种可怕而不寻常的嘶鸣的嘴巴,它伸出来了,倒下去了。于是,这个地点立刻聚起一群人,他们停留在那里,听得到他们嘶哑、低沉的说话声和一下短促的射击声,然后人们又默默地、无止境地往前走。我坐在这块石头上已经一个小时了,大家都绕过我走去,那大地,那空气,以及远处那些幽灵般的队列,则依旧那样地在颤抖。让人受不了的炎热又折磨着我,我也已经不记得瞬息之间自己头脑里想的什么了,而人们依然绕过我在走呀走的,我却不明白他们都是谁。一小时之前,我曾经一个人坐在这块石头上,而现在,我的周围已经集合起了一堆灰溜溜的人:有些一动不动地躺着,也许,是死了;另一些是坐着,并像我一样直愣愣地望着走过去的人们。有些有枪,所以他们像士兵;另一些人则几乎脱光了衣服,身上的皮肤又红得发紫,让人不愿去看。离我不远处有个什么人,光身子,背朝上躺着。因为他若无其事地把脸紧紧贴在尖利炽热的石头上,凭他一只翻过来的苍白的手掌,可见他是死了,然而他的背部却是红红的,像活人的一样,只是一层表皮像熏肉似的稍稍有点儿发黄,说明他是死了。我想离开他远点儿,但是没有力气,便身子摇摇晃晃地张望着那没完没了走着的幽灵般晃悠着的队伍。根据自己头部的情况,我知道自己确实也快要中暑了,不过我处之泰然,就好像在梦中——死亡只不过是一段奇妙而杂乱无章的幻境道路罢了。
接着我看到一个士兵怎么从人群中走出来了,他坚决地向我们这边走来。刹那间,他掉进了一个壕沟里,而当他从那里爬出来并重新走路时,脚步并不稳健,让人感到他是在用最后一点力气恢复自己那疲劳到已经散了架似的身子。他就这样直接朝着我走来,我的脑袋已经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我感到害怕,问道:
“你要干什么?”
他好像只等着我说话似的停下来了;他站在那儿,身材魁梧,一脸大胡子,衣服领子撕开着。他没有枪,裤子只靠一个纽扣吊着,破口处可以看到他身上白白的皮肉。他的两只手和一双腿脚都叉开着,不过看得出他是竭力想把四肢收起来,却力不从心——两只手刚刚收起来,它们立刻又耷拉下了。
“你怎么了?你最好坐下。”我说。
可是他站在那儿,毫无效果地收拾着自己,同时默不作声地瞅着我。于是我不由得从石头上站起来,身子摇摇晃晃地盯着他的一双眼睛——从中看到的,是无限的恐惧和疯狂。大家的瞳孔都变小了——而他的两个瞳孔却都扩大到整只眼睛;通过这两扇巨大、黑色的窗子,他看到的,该是怎样一片火的海洋!也许我觉得他的目光里或许只有死亡——可是不,我没有错:在这两个乌黑无底的、由细小的橙黄色圆圈围着的像鸟儿那样的瞳孔里,表现出比死亡、比对死亡的恐惧更多的东西。
“你走开!”我边后退边叫嚷,“你走开!”
接着,他便好像只等我开口说话那样——这个还是那么魁梧、叉开着四肢和默不作声的人,他向我扑过来,把我撞倒在地上。我哆哆嗦嗦把被压住的两只脚挣脱出来,一跳而起,想逃跑——离开人们到一边去,到太阳晒着的没有人的和正在颤抖的远处去,这时左边山顶上传来轰隆一声射击,然后又是两下,那声音慢慢的,听起来像回音。头顶上有个地方,爆炸了一枚榴弹,同时响起人数众多的欢乐的尖声嚷嚷、呐喊和呼叫。
我们的退路被截断了。
已经不再感到要命的炎热了,那种恐惧和疲劳也消失了。我的头脑是清清楚楚的,思想明确而尖锐;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正在集合的部队时,看到人们的已经变得开朗的和好像是高兴的脸,听到他们嘶哑而大声的说话、命令和嬉笑声。太阳好像升得更高了,为了不妨碍我们,它变得暗淡了,静悄悄的了——空中又爆炸了一枚榴弹,同时传来一阵像巫婆发出的欢乐的尖叫。
我走了过去……
<strong>片断二</strong>
……差不多全部的马匹和炮手。第八连那边也是这样。在我们第十二连,到第三天快结束时,只剩下三门炮了——其余的都被摧毁了,还剩下六名炮兵和我一个军官。我们已经二十个小时没有睡觉,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三天三夜了,恶魔般的轰鸣和尖叫像疯狂的乌云紧紧包围着我们,把我们和土地、和天空、和自己的人们分隔开来——于是我们几个活着的人,像梦游者似的在游荡。死去的,他们安安静静地躺着,而我们则在活动,干着自己的事情,说着话,甚至还笑——像梦游病人一样。我们的活动是自信而迅速的,命令清楚,执行准确——但要是突然问每一个人他是谁,在他稀里糊涂的头脑里未必能找到答案。好像是在做梦,所有的面孔似乎老早就认得,以前老早就知道;可是当我开始凝神注视某一张脸或某一门炮,或者听到轰鸣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又以各自的新颖和无穷的神秘莫测使我感到惊讶。夜幕不知不觉间降临了,而且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它便感到奇怪起来:这夜它到哪里去了?太阳怎么又在我们头顶上燃烧起来了?只有从到来的一些人那里我们才弄清楚,战斗正在进入第三个昼夜,但又立刻把这事儿忘了:我们感到奇怪了,这全都是在同一天,没有结束,没有开始,它忽而昏暗忽而明亮,却同样不可思议,同样盲目。所以我们这些人当中没有人怕死,因为谁也不明白什么是死亡。
我不记得在第三夜还是第四夜,我靠在胸墙上才一分钟,而且是刚闭上眼睛,头脑里便出现了那个既熟悉又不寻常的景象:一小片浅蓝色的壁纸和我的小桌子上那只因为没人用而落满灰尘的长颈玻璃瓶。还有在隔壁一个房间里——我看不见他们——好像待着我的妻子和儿子。不过现在我的桌子上点着一盏带绿色罩子的灯,这就是说,现在是傍晚或夜间。这景象一动不动地停留在那儿,我则长久而非常平静、非常仔细地在观察,看那灯光怎样在长颈瓶的玻璃上嬉耍,而且边看边想:儿子为什么没有睡觉,已经是夜晚了,是他该睡觉的时候了。然后又细看那壁纸,那上面所有的弯弯扭扭的图纹、银白色的花朵、格子和管子——我从来不曾想到我对自己的房间知道得这么清楚。有时我睁开眼睛,便看见黑黝黝的天空带着片片红色的火光,于是重新闭上眼睛,又重新端详壁纸、闪闪发亮的长颈玻璃瓶,并在心里想:儿子为什么不睡觉,已经是夜晚了,他也应该睡觉了。有一次,一枚榴弹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我的两条腿被什么东西摇动了一下,有人大声在嚷嚷,嚷得比爆炸声还响亮,我于是想:有人被打死了!但是我没有站起来,而且没有使眼睛离开那蓝兮兮的壁纸和长颈玻璃瓶。
后来我站起来,来回走着下达命令,查看人员,调试瞄准器,而自己则一直在想:儿子为什么没有睡觉?关于这事儿,有一次我问驭手,他也久久而仔细地对我解释了什么,而且我们两个人都点了点头。他还笑了,可是他左边的眉毛抽搐了,一只眼睛对后面什么人狡黠地眯了眯,而朝后面所看到的是谁的鞋后跟——此外再没有什么了。
这时已经天亮了,突然间掉起了雨点。这雨——和我们那儿的一样,是些最普通的小水珠子。它下得这么突然和不是时候,我们大家又都那么怕被淋湿,以致都丢下炮,停止了射击,开始找个随便什么地方躲起来。和我刚说过话的那位驭手爬到炮架旁边,凑合着把身子蜷缩在那儿,也顾不得自己分分秒秒都会被压死。胖胖的炮兵士官不知为什么开始去脱一个死者的衣服,而我则在连里急急忙忙走来走去寻找什么东西——不知是风衣还是雨伞。由于飘过来一片云,雨下大了,于是整个茫茫的空间里顷刻之间变得异常地寂静。一枚发射晚了的榴霰弹尖叫了一声炸裂开了,然后变得太安静了——静得啊,连胖胖的炮兵士官的打呼噜声以及雨珠子落在石块和炮上的声音都听得见。这种平静的淅淅沥沥的碎雨声使人想起秋天,而土地淋湿后的气息和宁静——仿佛刹那间打断了这场血淋淋的和野蛮的噩梦,于是当我瞧了一眼被雨水浇湿的发亮的大炮时,它突然荒唐地使人回想起某种亲切、静谧的东西,有些像自己的童年,也有些像初恋。然而,远处传来特别响亮的第一发射击声,迷人的寂静瞬间消失了;大家和突然躲起来的时候一样,突然从自己的掩体里爬出来;肥胖的炮兵士官对着一个人大叫大喊;轰隆一声炮响,接着又是一声,血淋淋密匝匝的浓雾又重新遮住了受尽折磨的大脑。所以,谁也没有觉察到雨什么时候不下了;我只记得水怎么从被打死的炮兵士官,从他那张肥肥胖胖脏兮兮发黄的脸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淌——显然,这次的雨连续下了好长时间……
……我面前站着个年轻的预备役士官生,他把一只手举到制帽上敬礼,同时报告说,将军恳求我们只坚持两小时,到那时一定会有增援部队来。我心想着我的儿子为什么没有睡觉,回答说要坚持多久我就坚持多久。但这时不知为什么他的脸使我发生了兴趣,大概是因为它苍白得非同寻常和令人吃惊吧。我没有见过比这张脸更白的了:甚至死人的脸都要比这张年轻的、还没有长胡子的脸多一点光泽。该是他到我们这里来的一路上给吓坏了,却没有能恢复过来;后来,他那只手一直贴在帽檐上,为的是用这个习惯的和简单的动作,驱散那令人心惊肉跳的恐惧。
“您害怕?”我捅了捅他的一只胳膊问。但那只胳膊像根木头,而他则一声不吭地微笑着。更确切点说,他脸上参与微笑的只有他的抽搐着的嘴唇,一双眼睛里却只有青春和恐惧——别无其他。“您害怕?”我亲切地重复问道。
他的嘴唇在抽搐,竭力想说出话来;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某种让人莫名其妙的、古怪得出奇的和超寻常的情况。一股暖风吹到我的右脸颊上,使我剧烈地摇晃了一下——在我眼里刚刚还是苍白的这张脸上出现了一道短短的、圆头的、红色的玩意儿,不知从哪里流出一道血,就像用一只去掉塞盖的瓶子在蹩脚的招贴画上画画。而那微笑,通过短短的红色的流淌的玩意儿仍在继续,一种疯狂的笑——红笑。
我认识了它,这种红笑。我一直在寻找,终于找到它了,这红笑。现在我清楚了,所有这些畸形丑陋、支离破碎和古怪的躯体是什么意思。这是红笑。它在天空中,它在太阳里,而且它将很快流散开来,流遍整个大地,这种红笑!
而他们,清清楚楚而又视若无睹,像一些梦游病人……
<strong>片断三</strong>
……疯狂和恐惧。
人们在讲述我们和敌方的军队里都有很多人患了精神病。我们这里设立了四个精神病房。我在司令部的时候,副官带我看了……
<strong>片断四</strong>
……像是被一些蛇缠绕住了一样。他看见铁丝网的一端被剪断后翘到空中,缠住了三个士兵。铁丝扎破了军服,刺进身上的肌肉里,士兵们便叫着嚷着不要命地在打转。后来,一个还活着的把两个死了的从自己身边推开,那两个便歪歪斜斜地转动着,其中一个倒在了另一个的身上,他们又都压在了他的身上——结果一下子三个人都一动也不动了。
他说,光在这一道篱笆墙下牺牲的人就不少于两千。他们在砍铁丝网并为像蛇一样弯弯曲曲的铁丝感到害怕的时候,子弹和霰弹像雨点般地向他们落下来。他要人相信,当时的情景很可怕,要是有个方向可以逃,这次进攻一定会以他们惊恐万状的逃跑告终。但是,十道或十二道没有断口的铁丝网墙以及与它们的搏斗,整个底下插满尖桩的迷宫似的陷阱,把头脑完全给搅糊涂了,简直没法确定方向。
有些人像瞎子似的掉进深深的管道形陷坑里,肚子被削尖的木桩挂住了,便像一些玩具小丑似的在那里乱颠挣扎;新掉下去的人压在他们的身上,很快整个陷坑被填得满满的,大堆血淋淋的活人和将死的人在蠕动。到处是从底下向上伸出来的胳膊,那些痉挛着弯曲起来的手指竭力把掉进陷坑、已经再也没法挣脱出来的人抓住:数百个有力而盲目的手指像紧紧夹起的虾螯蟹足,抓住衣服把别人往自己一边拉,戳进别人的眼睛里,以及把别人掐死。许多人像喝醉了酒,在往铁丝网上跑,到那里被钩住后就开始大叫大喊,直到他们被子弹结果了生命。
总之,他觉得大家都变得像一群醉鬼:有些人互相破口大骂,另一些人则哈哈大笑,当他们的一只手或一条腿被铁丝网钩住了,那时也就死在那里了。他本人呢,尽管打一清早没有喝过也没有吃过什么,还是感到自己怪怪的:头晕,恐惧不时为疯狂的欣喜所代替——一种恐惧的欣喜。和他并肩站着的人开始唱歌了,他就顺着人家唱下去,歌声很快变成完整并很和谐一致的合唱。他不记得当时唱的什么歌,但是是一种很开心的、配合跳舞的玩意儿。是啊,他们在唱歌——可是四周围的一切却因为在流血而呈现出一片红色。天空本身好像成了红的,而且可以认为,宇宙间发生了某种灾难,某种古怪的变化和色彩的消失:浅蓝的和绿的以及其他一些习惯的宁静的颜色消失了,而太阳在燃烧,放射出红兮兮的五彩的火焰。
“红笑。”我说。
但是,他不明白。
“是啊,还哈哈大笑呢。我已经对你说了,像一群喝醉了酒的人。也许,当时甚至还跳舞了呢,好像是的。至少,那三个人的动作像在跳舞。”
他清楚地记得:当他因胸部中弹负伤倒下去的时候,直到丧失知觉的一段时间里,他的两只脚还翘了几下,好像是在给谁伴舞。而且现在他回想起这次进攻的战斗来,仍带着一种好奇的感觉:一部分是因为害怕,一部分则仿佛是有想再经受一次那种情景的希望。
“还想让子弹再穿过胸部一次?”我问道。
“是这样的:并不是每一次都会被子弹打中的。伙计啊,要是得到一枚勇敢勋章,就好啰。”
他仰脸躺在那儿,脸色发黄,鼻子尖尖的,颧骨突出,一双眼睛凹下去了——像个死人似的躺着,还在幻想获得一枚勋章。他身上已经开始溃烂了,发着高烧,再过三天就该把他扔进坟墓里去,和死尸一起,可是他躺着,露出幻想的微笑,还说勋章。
“给母亲发电报了吗?”我问。
他变得惊恐和严峻起来,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于是我也沉默了,听到了伤员们在呻吟和说胡话。但是当我站起来要走时,他伸出一只滚烫而且有力的手握住我的手,以自己两只深陷进去的眼睛,惘然和忧伤地盯着我。
“这到底是怎么了,啊?到底怎么了?”他拉拉我的一只手,坚决地问。
“什么呀?”
“哎,总的说嘛……所有这一切。因为她等着我。我不能死啊。祖国——啥叫祖国,难道你能对她说得清楚吗?”
“红笑。”我回答说。
“啊呀,你总说笑话,可我是认真的。必须解释清楚,但是难道能对她解释得清楚吗?如果你知道她在信中都写了些啥?她写了些啥?你也不知道,她写的——是一些老话。而你……”他好奇地看了一眼我的脑袋,伸出一个手指捅了捅,然后出人意料地笑起来说,“你可是谢顶了。你注意到了吗?”




![[综]如何温柔地杀死狂犬](https://jmvip2.com/images/26594/962cda787fe9573732249a9f34887ac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