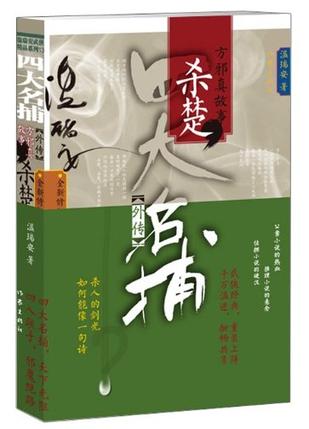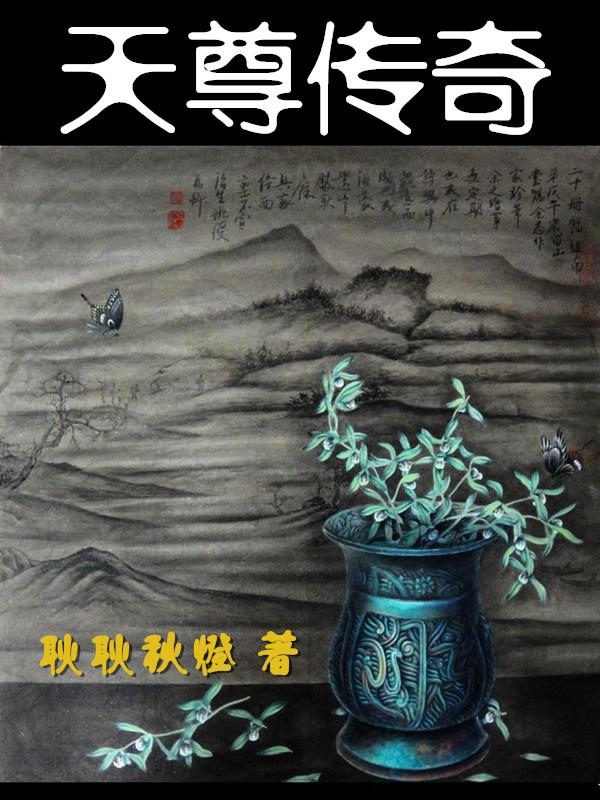丹·西蒙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1
1925年4月25日,星期六
珠穆朗玛峰依旧在40英里[1]开外的地方,可在喜马拉雅山脉众多白色高峰的轮廓线之中,它依然是最显眼的一座,抬头望向天空,能看到的就是这座高峰。我怀疑理查带了一面英国国旗来,准备将它插到峰顶上。不过现在我可以看到,这座高山已经有了细长三角旗。一片白色的云雾和浪花溅沫般的飘雪,在自西向东的狂风吹拂下,滚滚翻腾着,足有20英里长;在珠峰雪顶的东面,一片白色羽状物在较低的山峰上方从右到左打着旋儿。
“我的天哪。”让-克洛德低声说。
算上帕桑在内,我们一行五人在前徒步跋涉,夏尔巴人挑夫赶着牦牛在后,我们几个爬上了庞拉山口东面一座低矮的山峰,帕桑站在我们身后几码[2]远的地方,位于山口高点之下,抓着J.C.那匹小白马的缰绳,庞拉山口上的风太大了,这匹马受了惊。过了庞拉山口,就到了绒布冰川和珠峰。此时我们四个人只能躺在砾石散落的地面上,否则就会被风卷走。
我们随随便便向右侧躺着,很像罗马人在宴会上躺在长榻上一样,理查离我最远,用右手手肘支撑身体,左手稳稳拿着军用望远镜;他旁边是雷吉,她俯在地上,靴底看起来像是倒转的感叹号,她用双手扶住一个海军式望远镜,抵在她前面一块低矮的砾石上;她的旁边是让-克洛德,他比我们几个坐得都直,眯缝着眼睛透过护目镜看着南方;最后是我,我靠着右手手肘斜撑着身体,处在他们三个人的后面。
我们几个都戴着宽边帽子,好遮挡阳光,在这样的海拔高度,阳光毒辣得要命,在前几个星期里,我被晒得快着火了,身上直脱皮,难受得不得了,显然桑迪・欧文曾经也受过这罪,我们三个男人把我们脑袋上的帽子尽可能向下拉,以便抵御狂风,而雷吉则戴了一顶非常奇怪的男士软呢帽,左面、前面和后面的帽檐很宽,右边则用纽扣扣住,帽子上有可调节的带子,绕过她的下巴,把帽子系得非常紧。她说她是在几年前去澳大利亚时无意中找到了这款帽子。
我们一个个叫出群山的名字,像是小孩子在大声说出圣诞礼物:“在西边,那座高山名叫卓奥友峰,海拔26,906英尺[3]……”“格重康峰,25,990英尺……”“那座把阴影投射到珠峰上的山峰是洛子峰,海拔两万七千……我忘了……”“27,890英尺。”“东面那里是珠穆隆索峰,25,604英尺……”
“还有马卡鲁峰,”理查说,“27,765英尺。”
“我的老天。”我又一次低声说。人们可以征服美国落基山脉的最高峰,但对于这些有着白色山尖的巍峨高山,他们或许就连山麓小丘都无法翻越。那些山坳,也就是那些鞍状山口,是连接珠峰和其他山峰之间的低点,最低海拔高度也有25,000英尺,比北美任何一座高山都高出3000英尺。
据雷吉和理查说,一般情况下,前面几支探险队队员在向西前往协格尔镇的徒步跋涉途中都能看到珠峰,特别是如果他们愿意绕道定结县以西的雅鲁山谷,向上爬一段距离,就能把珠峰看得更清楚了,可过去五个星期我们都是顶着厚厚的低矮云层艰苦跋涉,时常还要冒着冻雨和飞雪前进,因此,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庞拉山口顶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那座山。
雷吉示意我向前,我趴伏在她的身边,身下是发红的泥土和坚硬的岩石,这还真是一个奇异的亲密时刻呢。她把镜筒弄稳,好让我透过望远镜往前看。
“我的老天。”这似乎是今天我唯一会说的几个字。
虽然我年纪不大,在锡金的时候我度过了我的二十三岁生日,可我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登山经验,所以我很清楚,一座山从远处看似乎无法攀爬,可到了特别近的地方或者到了山上,就能发现攀登路线,或许还会有极易攀爬的路线呢。可珠穆朗玛峰看上去……是那么巨大、那么高耸、那么白,风是那么大,而且无限遥远。
让-克洛德爬过去借用理查的望远镜。
“从这里看不到北坳或东绒布冰川的高点,因为中间有很多山挡住了视线。”理查说,“不过朝东北山脊看,能看到靠近顶峰的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吗?”
“我能看到的只有无边无际的浪花溅沫般的羽雪。”让-克洛德说,“现在东北山脊上刮的什么风?”
理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深峡谷,他们现在都称之为诺顿的大深峡谷,从顶峰三角岩下方一直向左下延伸。”
“噢,是啊……”J.C.低声说。
透过雷吉那个两个镜筒贴得太近的望远镜,我压根儿不可能看清那道峡谷是否填满了雪,是否是个雪崩随时会爆发的夺命之地。
“春季的狂风真是太好了。”雷吉说,庞拉山口上狂风大作,呼啸着,咆哮着,从砾石之间刮过,她的声音几乎被风吹散了,“风吹走了季风季节和冬季的积雪。这样我们就有更大的机会找到珀西了。”
珀西。我越来越迫切地想赶快去到那座山,开始攀登,几乎把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事儿和我们不远万里来到此处的表面原因抛到了脑后。一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尸体就在那座难以攀登且异常危险的高山上的某个地方,而且令人无法忍受的狂风在那里肆虐,我便不由得浑身发抖。
帕桑强有力的声音自较低的地方传来。“最前面的挑夫已经快到我们后面的山口顶端了。”
又是被狂风吹,又是顶着自始至终都毒辣辣的太阳眯着眼看远处的那座山峰,我们疲劳的眼睛开始泪流不止。我们四个人不情不愿地站起来,把一层层沉重的鹅绒和羊毛衣服上的灰尘和石子弹掉,转过身,后背对着从西面吹来的大风,走向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翻越这座鞍状山口。狂风吹着我们的后背,我们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
*
锡金遍布着各式温室花朵,有一丛丛杜鹃花,空气浑浊潮湿,呼吸起来十分不顺畅,杂草丛生的山谷里热气腾腾,扎营的空地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空地。漫漫长日里,我们徒步穿越湿漉漉的植被,还要躲开驿站,到了一天结尾的时候,盐分都从我们身体里滤了出来。所谓的驿站就是英属印度设立的小平房,很整洁,每隔11英里(徒步行进一整天才能走11英里)有一个,位于一条很长的通向西藏的主路上,而这条路正好延伸到最近的一个西藏贸易市镇江孜镇。据雷吉和帕桑医生介绍,每一座驿站平房里都有新鲜的食物、床、可以阅读的书,和一名常设仆人,人称守卫。不过我们一队人要么是在驿站前1英里左右的地方扎营,要么是在过了驿站2英里处扎营,从来没有利用驿站之便,尽管这些驿站被设立在那里,就是为照顾我们这样的人。
“几支英国探险队都住在驿站里。”进入锡金的丛林后不久,我们围坐在篝火边,理查说道。
“其他几百位英国人也这样,”雷吉说,“还有向北去江孜镇的贸易代表、英属印度的官员、剥制动物标本的人、制图员,外交人员。”
“可我们不是这些人,”理查说,“看到我们的登山设备,好几英里长的绳子,那些仆从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消息传到西藏。”
“怎么把消息送出去?”让-克洛德问。
理查把他的烟斗拿开,浅浅地笑了。“先生们,其实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样,我们已经超出了所有地图的覆盖范围。即便是在锡金此地也是一样。英属印度架设了电话和电报线缆,一直向北,翻越那些高山山口,连通了江孜镇。”
“一点儿不错,”雷吉说,“我们不能离开这条南北主贸易通道,之后我们才能转向西面,向康巴镇前进,进入西藏。不过呢,不去驿站里相对舒舒服服地过夜,而是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扎营,我想我们唯一要对付的就是那些水蛭。”
出发时我们先从大吉岭向下前往提斯塔桥。3月26日,那些夏尔巴人在天亮之前就出发了,他们牵着马,背负着装备,我们则带着我们的背包和额外的给养坐在两辆卡车里,一辆由帕桑驾驶,雷吉则是另一辆,沿着崎岖不平的路到了第六英里石。在那里我们赶上了这些徒步前行的夏尔巴人,而司机爱德华和另外一个人把卡车开回了种茶场。然后,我们和30名夏尔巴人一起,骑着马,牵着骡子,继续沿陡峭的山路下山,跨过提斯塔河,前往噶伦堡村。
过了噶伦堡我们就扎营了,因为雷吉不愿意这么快就引起锡金总督弗雷德里克・贝利少校的注意,此人反复无常,专门搞破坏,不让珠峰委员会拿到进藏许可,这样一来,有朝一日他就有机会自己去爬那座山了(这事儿是雷吉告诉我们的)。我们进入锡金境内时遇到了一位边防人员,他是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廓尔喀士兵,只有他一个人在此驻守,他认可了雷吉的西藏通行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这位孤零零的边防人员居然冲自己喝令:“右手敬礼!”“左转!”“齐步走!”我们都被逗笑了。后来理查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长官或者军士给这些廓尔喀士兵喝令,他们就会非常高兴地把自己命令得团团转。
我们在锡金境内一共走了六天,途中两次碰到穿警察制服的棕色皮肤男人,他们截住了我们这支由夏尔巴人、骡子和白色小马组成的队伍。不过每一次雷吉都把这些官员拉到一边,私下里和他们说话,而且我猜她还给了他们钱。不管怎么样,在锡金境内没有人阻止我们,连着一个星期,我们呼吸着过分香甜的杜鹃花花香,每每涉水穿过及腰深的潮湿草地之后,就得把水蛭从我们未加衣着的身体部位上拔掉。然后,我们终于接近了加里普山口,过了这座山口,就是西藏了。离开锡金我们一点儿遗憾都没有;那里阴雨不断,没多久我们的衣服就都被浸透了;没有一天能见到阳光,晾干衣袜。我原以为自己是唯一在穿越锡金途中患上轻度痢疾的人,结果我很快发现,让-克洛德和理查也得了这病。唯有雷吉和帕桑似乎对这种令人尴尬不已的疾病免疫。
在我自己吃了好几天的鸦片铅丸之后,理查终于注意到我生了病,让我去找帕桑医生看看。我不好意思地承认我的肠道出了问题,结果这个大高个夏尔巴人点点头,轻声告诉我,鸦片铅丸对痢疾倒是有一点儿疗效,可夜里吃这药带来的副作用会比这病本身还要严重。他给了我一瓶甜甜的药,不到一天我的肚子就消停了。
一开始,我都是走在我的白马前面,背着包里大约70磅[4]重的装备,不过雷吉说服我,让我在能骑马的时候就骑马,并且让骡子驮着我的大部分装备。“你得保存体力,到珠峰上去用。”她说,很快我就意识到她说得太对了。
得了痢疾,我的身体有些虚弱,后来便开始慢慢恢复,这期间我已经适应了我们的探险队一到傍晚便停止前进这个习惯,而夏尔巴人开路小队已经搭好了温伯尔帐篷和用来做饭的大防水布帐篷,我们睡袋也铺好了,只等着我们到来;巴布・里塔和诺布・切蒂每天早晨都会给我和让-克洛德端来咖啡,我习惯一听到他们轻声说“早上好,大人们”这句话就醒来。理查在我们隔壁喝他的咖啡,而雷吉总是比我们任何人都早起且穿戴整齐,她会和帕桑一起在火边喝早茶,吃松饼。
一直到我们攀登14,500英尺的加里普山口,我才意识到在锡金患过的那场病给我的身体带来了多大的损伤。几年前,我和哈佛大学的登山好友一起在科罗拉多攀登14,000多英尺的朗斯峰,我可以飞快地登上顶峰,站在宽阔的山顶感觉激情澎湃,而且还能倒立。可现在在向加里普山口顶端攀爬的过程中,既要攀登之字形山路,还要翻越湿滑的岩石,这些石头倒是有点儿像无穷无尽的天然楼梯,我发现自己走出三步便要靠在我的长冰镐上喘大气,然后再走三步。这座山口的制高点还不到珠峰海拔的一半,所以我这个样子可不是个好兆头。
我看得出来,让-克洛德的呼吸也有些急促,移动速度比以往稍慢了些,尽管他登顶过许多座14,000多英尺的高山。我们原本的三人组合中只有理查一人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海拔,我注意到,他依旧很难赶上雷吉徒步行进和登山的飞快步速。
我们到达了西藏的亚东县,西藏和锡金这两个地方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在加里普山口的高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亚东县,在我们向干燥的西藏高原行进的过程中,雪不停下着,狂风不住从西面吹来。走出了姹紫嫣红的锡金丛林,那里有粉色、有浓艳的奶油色,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颜色,不过雷吉和理查认出那些是淡紫色和鲜红色,我们来到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无色世界,乌云低沉,仿佛就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周围尽是灰色的岩石,唯有西藏当地暗红色的土壤为这片大地增添了一点点色彩。狂风卷起红色泥土,很快我们的脸都变得脏兮兮的,而且冷风吹得我们直流眼泪,粘满泥土的脸颊上留下了一道道泪痕,流下的泪水犹如鲜红的血液。这之后我才意识到,即便是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也应该带上护目镜。
*
4月27日,星期一,这是我们徒步跋涉的最后一天,我们在狂风肆虐的小村庄初东村外过夜,转过天来,我们穿过一条18英里长的山谷,朝绒布寺进发,绒布寺距离绒布冰川的入口只有11英里远,而我们的大本营就应该设在那里。
“绒布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问。
理查可能不知道答案,也可能心事重重,所以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雷吉给出了答复:“雪之寺。”
我们在这座暴露于狂风之中的寺院停留了很长时间,请求拜见神圣喇嘛,札珠雅旺滇津诺布仁波切,也就是札珠仁波切活佛,希望他能为我们做一场赐福法式。“夏尔巴人不像藏族挑夫那样笃信这个,”在我们等待期间雷吉解释道,“不过在我们动身前往大本营之前,得到这样的赐福依然是一件好事儿,何况我们还要去攀登珠峰。”
可我们的愿望破灭了。这个名字听起来像锡罐从混凝土台阶上滚下来时发出声响的喇嘛叫人捎信来说,此时他与我们见面“不祥”。这位神圣喇嘛派来的人说,如果神圣喇嘛感觉他出现给我们赐福是吉祥的,那么札珠仁波切将召唤我们回到绒布寺。
雷吉对此感觉非常惊讶。她说,不管是绒布寺里的普通喇嘛,还是这位神圣喇嘛,她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不过当她问到一位她认识的喇嘛,为什么札珠仁波切拒绝见我们,这位光头老人回答了她,他说的是藏语,雷吉给我们翻译了过来,意思就是:“占卜结果大不利。那座山上的魔鬼已经苏醒,十分愤怒,更多的魔鬼即将到来。珠峰上的人熊雪人活跃起来,愤怒异常……”
“人熊雪人?”让-克洛德问。
“耶蒂,”理查提醒我们,“就是那些无处不在长满毛发的类人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