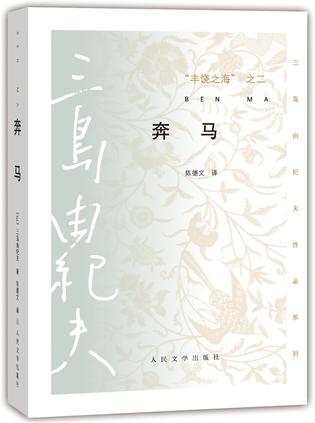丹·西蒙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1925年5月15日,星期五
我们在中午之前回到了大本营。那里差不多成了一片废弃的营地。
当然了,帕桑医生还在那里,他那两位被冻伤的病人还在他们的帐篷里养病。昨天所有人从绒布寺回来之后,帕桑进行了截肢手术:昂・蚩力的十根脚指都没了;拉帕・伊舍则失去了四根脚指和右手的三根手指。帕桑告诉我和J.C.,正常情况下,他会再等很长一段时间才做手术,可从昂・蚩力的脚指开始,溃烂已经扩大到了整只脚,坏疽也在威胁拉帕的右手和左脚。
我和让-克洛德去看望他们俩:昂・蚩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兴,他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试试放在他登山靴脚指位置的木楔,看看在没有真正脚指的情况下走路是什么样子。我和J.C.都产生了一个想法,却没有大声说出来:一个夏尔巴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中穿着凉鞋走路,并不会穿英国制造的登山靴。可很显然昂倒是不在乎这其中的细微区别。
拉帕遭受的创伤没有昂严重,却要沮丧得多。他们两个人的脚上都缠着绷带,红黄色的碘酒浸透了绷带。拉帕轻轻捧着他那只现在只剩下两根手指的右手,一边流眼泪,一边叨叨。据帕桑翻译,他是在说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来到帐篷外,我和J.C.说起了昂・蚩力的高昂斗志,帕桑则轻声说:“永远不要怀疑在术后使用一点点鸦片带来的效果,那东西可以令人精神振奋。”
大本营里只有大约五个夏尔巴人,帕桑告诉我们,昨天雷吉和理查给大部分夏尔巴人都分配了背运任务,把装备都背到“高处的营地”去,即在最后一道冰坡底部的三号营地和北坳之上的四号营地。帕桑还说,今天有人捎信下来,山上狂风大作,暴雪特别大,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北坳下面,只有理查、雷吉和两个老虎夏尔巴人上去了。而且据帕桑猜测,现在就连他们这四个人或许也退回了三号营地。至少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有很多顶帐篷、睡袋和食物,可以供多人住进去或整休。
帕桑对我们说,他自己也很着急要到更高的营地去,只要他的两个病人病情见缓,他就动身。当然了,他能不能恢复自由,还要看有没有人再受重伤,以至于他只能把伤者送回大本营医治。照我猜测,帕桑只是不愿意和他的雇主,也就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分开这么久。
我和让-克洛德决定要把装备背到今天我们所能到达的最高营地去,虽然我们从大本营出发的时间比较晚。我看我俩都太需要来一次洁净的登山之旅,把装备背上去,一扫黎明时分的阴霾。我知道我会做到。
很多吸氧装备已经被夏尔巴人运去了较高的营地,我和J.C.尝试搬运两套装在背物架上的整体氧气罐,这六罐氧气几乎无一渗漏,我们缩身套上了安全带,准备在夜幕降临之前把这两套吸氧装置背上我们所能登上的最高处。
把欧文和芬奇改良过的吸氧装备背在背上——今天我们不会吸一口英国的空气,所以面罩和阀门都塞在金属框架里——我们背运的东西就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理查规定的负重标准上限25磅,不过我们还是背了一些个人物品,以备在哪个高处营地停留之用,或许我们要在那里一直待到尝试登顶的一刻呢。于是,我们用了两个卡肩式前背包,这东西其实是一战期间用来装防毒面具的袋子,是理查买来的(可没买防毒面具),很便宜,他买了很多。这种背包好用极了,可以塞进我们的个人物品,包括额外一些衣物,剃须工具包——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用这些东西了,因为我挺讨厌用冷水刮胡子——照相用具,卫生纸,等等。高处的营地里可能有多余的睡袋,不过我和J.C.都不想冒险:我们把睡袋紧紧地卷起来,罩上防水保护套,然后绑在了氧气管框架的外金属杆上。
我们带上了那些尺寸不一的奇特冰镐(只把长冰镐放在外面,不和其他东西系在一起)和两个J.C.的祝玛,并穿上了12爪冰爪,用带子将之绑好(虽然去二号营地的大部分路途都要在冰碛石上穿行)。今天冷得要命,雪也非常大,我们穿上了芬奇的羽绒外套和雷吉的羽绒裤子,外面套上了沙克尔顿夹克和滑雪裤。
我们离开时和帕桑握了握手,随后穿越肮脏的冰碛石壁和偶尔出现的几根冰柱,一路登上了布满岩石的河谷。天气依旧十分恶劣,可视距离只有15英尺。这里的风要比绒布河谷的大,落下来的雪似乎并没有积得很厚,坚硬的雪粒如同大号铅弹一样,刮到我们的脸上,弄得我们生疼。
我俩用一根40英尺长的理查奇迹绳系在一起,肩上还悬挂着更多的绳子,由我打头,我和让-克洛德一路向上穿越12英里长的河谷和冰川,向北坳进发。
*
我和J.C.先是登上了槽谷,随后攀上了二号营地上方的冰川,在这段漫长的徒步跋涉中只在必要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我们分别陷入了各自的思绪中。
我想到了山上的死亡。巴布因为我们的胡闹而白白丢了性命,我对他的死感到了真真切切的内疚。此外,我还想起了其他一些发生在登山时的死亡事件,以及我对这些死亡的反应。对于登山时的突然殒命,我并不陌生。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哈佛登山俱乐部一直到去年,也就是1924年才正式成立,可当我于1919年—1923年在哈佛求学期间,每逢假期和闲暇时间,在春天和秋天里我们几个人就去附近的昆西采石场登山,到了冬季则会去征服新罕布什尔州的山脉。在登山圈子里,我们几个人称“哈佛登山四人组”。
大学讲师亨利・S.霍尔是我们的非正式领队,我们这支特别登山队就在他家里开会,正是此人于1924年组建了哈佛的正式登山俱乐部。我们这个小队的另外两名成员是特里斯・卡特(与我同岁)和艾迪・贝茨,贝茨比我们小一岁,是个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堪称顽强的登山者。个子不高,他登山时会使用膝盖、手肘和快速移动的脚后跟,登山技术异常娴熟。
霍尔教授和他那些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的登山伙伴专门攀登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和阿拉斯加的落基山脉,不过攀登后者的时候并不多。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初秋学校放假,我们四个人去爬了加拿大亚伯达的神庙山,登上了东部山脊——现今这座山脊的攀登难度评级为IV5.7左右。艾迪失足了,拉断了一根60英尺长、连接着他、特斯里和我的绳子,不幸摔死了。我们并没有做保护,艾迪摔下来得非常突然,而且是垂直落下,如果不是绳子断了,我和特里斯肯定会和他一起掉下那面北壁。
当然了,艾迪的死令我们非常哀痛,我们用年轻人怀念同龄死者的特有方式表达悲伤。艾迪的父母来哈佛收拾他的遗物,我很想和他们说说话,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掉眼泪。开学之后,我开始翘课,就坐在我的房间里沉思。我肯定我再也不会去登山了。
这时候霍尔教授来看我。他告诉我,要么去上课,要么就退学。他说我现在这副鬼样子只是在浪费我父母的钱而已。至于登山嘛,霍尔对我说,只要下第一场雪,他就会带学生登山者去登华盛顿峰,还说我应该自己做决定,以后是不是要继续登山——他觉得我的登山技能倒算是可圈可点——还是从此与登山一刀两断。“但是,死亡是这种运动的一部分,”霍尔教授告诉我,“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很不公平,可客观现实就是如此,用绳子和我们连在一起的朋友或伙伴死了。如果你还想继续登山,杰克,你必须学会说句‘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
我从没听过哪位老师或教授说这三个字,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他传授给我的经验教训同样令我醍醐灌顶。
可在过去几年的登山经历中,我还是学会了说“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起码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这么做。在我、理查和J.C.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参加了不少于五次营救,其中三次都有人不幸遇难。诚然,遇难的登山者我一个都不认识,可我逐渐了解,人从山上掉下来,一定会被摔得支离破碎,不成人形:四肢张开,骨断筋折,摔下去的过程中衣服被凹凸不平的岩石扯破,血流各处,头骨被撞碎,或者身首异处。从高处摔死决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
巴布・里塔并没有从山上掉下来,他只不过是跟着两个傻瓜从一个斜坡上滑降下来。下雪的时候,在美国任何一座市政公园里,人们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带雪橇滑道的斜坡。只是那些滑道里往往不会有藏在雪下的砾石。
“他妈的,”我听到自己轻声说,“继续前进。”
*
狂风呼呼吹过槽谷中的冰柱,一登上冰川,我们就要挖出固定绳索,在穿越冰隙之际确保安全,不过那些插着旗子的竹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赶在天色开始发暗之前来到了三号营地,可雷吉和理查不在那里。三号营地里有六顶帐篷,其中两顶是超大号的米德帐篷,可我们却看到八个夏尔巴人都蜷缩在较小的米德帐篷里睡觉。彭巴呻吟着说他们都感觉很不舒服:全都得了“高山疲劳症”,1925年,我们都这样叫高空病。没有睡袋的人就裹着厚厚的毯子。彭巴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理查大人都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里,特比・诺盖和登津・伯西亚与他们在一起。据彭巴说,那里的风太大了。
我和让-克洛德退出这个臭烘烘的米德帐篷,商量了一下。天已经晚了,等我们到了四号营地时,天就该黑了。不过我们带了威尔士矿工头灯来,我的防毒面具袋里还有一个手电筒,我们俩都感觉自己浑身充满力气,而且没有耐性等下去。
说来也真够奇怪的,攀登最难的一部分竟然是从三号营地踩坑开路,向着那道雪坡脚下进发,然后在斜坡上徒步跋涉200英尺,来到第一根固定绳索开始拴系的地方。暴风雪和昏暗的天色遮掩住了害死巴布的那块砾石,可我还是不禁想象着,新落的雪下有一层冰冻的鲜血,就像是白面包下方涂抹的薄薄一层草莓酱。我们来到了斜坡比较陡峭的部分,固定绳索就在那里,我们只能用冰镐挖开新堆积的雪,找到固定绳索,并把它们从雪里拽出来。接下来,我们从帆布袋里找出了头灯装备,又拿出了那个小登山装备,让-克洛德按照他小时候养的一只狗的名字给这小装置取名为“祝玛”。他好像就是这么说的。
J.C.仔细做了检查,确保我已经把祝玛牢牢钳在理查的奇迹绳上,我说:“真是你发明了这个小装置?”
我的朋友笑了。“的确是我,不过是与我父亲合作的成果,那时候他帮一个名叫亨利・布鲁诺的法国年轻人打造一种装置,这个人希望能借助这个装置攀登山洞里自由悬挂的绳索。因为这东西是给一个人做的,所以我父亲没想着去申请专利,布鲁诺也没这个打算,他把他那种较大的洞穴探险绳索上升设备称为‘猴子’。我决定改良一下,把这东西做得更小、更坚固,从而增加安全性,并且采用较轻的金属打造,又增加了一个弯曲把手和把手防护装置,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伸进去了。另外我还设计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凸轮扣在绳索上,这样就不用害怕失足或绳子断裂了,瞧,就是这样!”
“不过‘祝玛’真的是你的狗的名字吗?”
让-克洛德笑只是回报给我一个更加灿烂的笑容,随后开始使用这个机械装置登山,我琢磨着应该把使用祝玛登山的方式称为祝玛式登山了。
*
一年前,不管是马洛里、欧文、诺顿,还是其他人,都用了四五个小时才能登上这面连接北坳的冰壁,尤其是遇到了我和J.C.碰到的这种打着旋儿的暴风雪的时候。在攀爬这面冰壁时,大部分时间马洛里差不多都是弯着腰,尽心尽力地用冰镐在冰雪之上开凿出新的踏脚处,因而累得筋疲力尽。我和J.C.把新冰爪的前尖刺进冰雪之中,同时借助祝玛向上攀登,只用了不到四十五分钟就登了上去,在这个时间里,我们还在半途休息了一下,悬在绳子上吃了几块巧克力。我们确实用到了长冰镐,可只是在向上攀登的途中用它来插进冰雪之中,以便在左手占用的情况下保持平衡,抑或用它来敲掉我们上方几码固定绳索上的冰雪。
暴风雪太大了,从冰架穿越北坳,前往位于北坳西北角高大冰塔之下的四号营地,这一段路程令人胆战心惊。可理查和其他人已经为我们打好了非常棒的基础,即便狂风肆虐,暴风雪侵袭,他们还是布置了稳固的竹枝和红色三角旗。如此一来,穿越这条路线简单得就像走在一条8英尺宽的高速公路上一样,虽然遍布着很多数百英尺深的冰隙,可这些缝隙都已经被标记分明了。
现在四号营地建起了一顶中型温伯尔帐篷,这顶帐篷是拆分开背运上来的,还建了RBT,也就是雷吉的大帐篷,以及两顶较小的米德帐篷,理查计划把运往更高营地的装备放在这两顶帐篷里。等这些东西被运上五号和六号营地之后,夏尔巴人在上下来往于理论上的补给线时就可以住在这些米德帐篷和温伯尔帐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