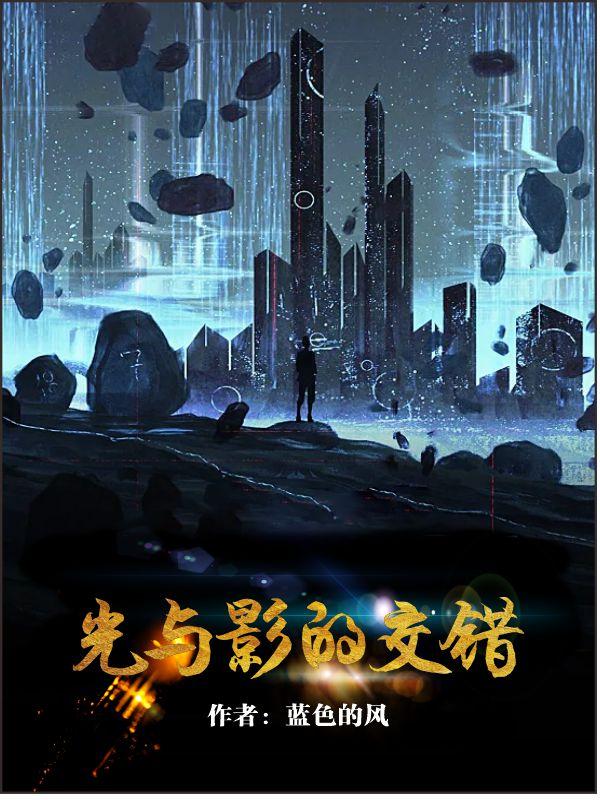丹·西蒙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整个索比堡只有三四个美国橄榄球球场大,却运转得十分高效。它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执行希姆莱的‘最终解决方案’。
“我认为自己这次死定了。我们下车后被赶到一道高篱笆后面,沿着一条铁丝网走廊往里走。他们在铁丝网中塞了茅草,我们只看得到一座高塔、树冠和正前方的两根砖砌烟囱。沿路的指示牌上写着我们要经历的三道程序——吃饭,洗澡,上天——充满了党卫军式的幽默。我们被送去洗澡。
“那天,从法国和丹麦送来的犹太人都在规规矩矩地走路,但我记得波兰犹太人很不老实,德国人一边咒骂一边用枪托驱赶他们。我旁边的一个老人大声辱骂他见到的所有德国人,还对脱他衣服的党卫军挥拳头。
“我已经想不起我进入浴室时的感觉了。我应该没有愤怒,只有一点儿生气。也许我最大的感受是轻松。近四年的时间里,支撑我的是一条简单的命令:我要活下来。为了执行这条命令,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胞、看着其他犹太人、看着我的家人被送入邪恶的德国屠杀机器的大口。不仅如此,我从某种意义上还帮助了德国人。现在,我终于可以歇息了。为了生存,我已经竭尽全力。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唯一的遗憾是,我杀死的不是上校,而是那个老人。那一刻,上校成了带给我无尽苦难的罪魁祸首。1943年6月,浴室的沉重铁门关闭时,我脑子里浮现出的就是上校的脸。
“我们挤成了一团,推搡,叫喊,呻吟。足足一分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管子开始震动,嘎吱作响。毒气就要来了。人们纷纷从喷头下躲开,但我没有。我站在喷头的正下方,抬起头。我想起了我的家人。我遗憾自己没有机会同母亲和妹妹道别。就在这一刻,仇恨终于填满了我的心胸。我怒火中烧,上校的脸占据了我所有的思维。人们大声哭喊,管子嘎吱晃动着,将里面的东西喷在我们身上。
“是水。水。浴室尽管每天都会用毒气杀死数千人,但同样每个月会给少数人真正的淋浴。浴室没有被封闭。我们被领到外面,除掉身上的虱子,剃了光头。我拿到一套囚服。我的手臂上被文上了一串数字。我想不起自己是否感到了疼。
“索比堡每个月都会选出少数囚犯来从事集中营的日常杂务。我们这拨人被选中了。
“我呆呆地回到刺眼的阳光下,仍然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但就在这时,我终于意识到,我被某种主宰命运的存在选中了,我活下来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依旧拒绝相信上帝——任何背叛了他的子民的神都不值得我信仰——但从那一刻起,我相信我能继续活下去,一定是有理由的。那个理由具象化为上校那张狰狞的面孔,我至死都会将它烙印在脑中。没有一个犹太人能说得清为何我们的民族会遭遇这场空前的灾难,更别说我当时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年,但我完全理解上校有多么邪恶。我要活下来。我要活下来,尽管我已经无法对活下来的命令做出反应。我要活下来,坦然应对命运施加给我的一切。我要活下来,就算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我也要消灭上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都住在索比堡的一号集中营。二号集中营是一个火车站。没有人从三号集中营里回来。他们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让我什么时候睡觉我就什么时候睡觉,让我什么时候排便就什么时候排便。我从事所谓‘火车站突击队队员’的工作。我披着蓝色袍子,穿着绣有黄色‘BK’标志的蓝色工作服。我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拨被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直到现在,我晚上都无法安睡。我常在梦中看见那些闷罐车,车上用粉笔写着那些人的来源地:图罗宾、格兹考、乌罗达瓦、希德尔斯、伊斯比卡、马库格佐、卡莫罗、扎莫斯科……我们从那些头晕目眩的犹太人手中接过行李,发给他们行李寄存单。因为波兰犹太人往往会激烈反抗——这减缓了屠杀的速度——我们只好故技重施,告诉那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索比堡只是中转站,在这里短暂休息后,他们将被安置到别的安置中心。有段时间,车站的站牌上甚至标出了到那些子虚乌有的安置中心的距离。火车不断将犹太人从各地送来:巴拉诺、里基、杜比恩卡、比阿拉泼拉斯卡、乌查聂、德姆布林、雷乔伊克……我们每天至少要寄一次明信片给那些仍在路上的犹太人。明信片的内容都是预先写好的:我们已经抵达了安置中心。这里的农活很重,但阳光很好,食物也好多了。希望能尽快见到你。犹太人被要求在明信片上写下地址,签好名,然后他们就被送进了毒气室。夏季快结束时,大部分犹太人隔离区都被清空了,就不再需要玩这个把戏了。康斯科沃拉、约泽福、米稠、格拉波维克、卢布林、罗兹——来自这些地方的火车都没有运来活人。这时,我们就只好将行李寄存单放在一边,爬上弥漫着腐臭味的车厢,将赤裸的尸体拖下来。这活儿我在切姆诺也干过,但这里的尸体有时会僵硬地搂抱在一起,因为火车偶尔会在郊外的岔轨上停留几天乃至几个星期,饱受烈日暴晒。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年轻女人同一个孩子和一个老妇人紧抱在一块儿。我去拉女人,结果竟然把她的胳膊拧下来了。
“我诅咒上帝,脑海中浮现出上校挂着冷笑的苍白面容。我要活下来。
“七月,海因里希·希姆莱访问了索比堡。那天刚好从西边运来了一批犹太人,所以他可以目睹屠杀的全过程。从火车到站到六个焚尸炉中的最后一缕青烟消散,总共不到两个小时。在此期间,犹太人的每一件物品都被没收、分类、登记、保存。就连女人的头发都在二号集中营剪下来,编成毡子,或者絮进U型潜艇士兵的拖鞋衬里。
“我在到达区搜检行李时,集中营司令官领着希姆莱及其随从经过。我对希姆莱没有多少印象——他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个子不高——但我立即认出了走在他身后的金发军官。是上校。上校两次俯身在希姆莱耳边低语,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转过头,对上校露出古怪的阴柔笑容。
“他们走到距我只有五米的地方。我弯腰工作,抬头偷偷瞟了上校一眼。他正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觉得他没有认出我。虽然我逃离切姆诺只有八个月,但在上校眼中,我肯定只是一个搜检死者行李的普通犹太人。这是老天赐给我的大好良机,但我犹豫了,于是一切都不可挽回。我觉得我当时可以够到上校。我可以在枪声响起前,掐住他的脖子。我甚至可能抢走希姆莱身边军官的配枪,在上校还未反应过来之前打死他。
“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阻止我动手的除了惊讶和犹豫之外还有什么。肯定不是恐惧。早在毒气室大门被关上之前的几个星期,我的恐惧就同我的其他感情一同消失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我犹豫了几秒,也许有一分钟,于是时机永远地丧失了。
“希姆莱一行继续前进,穿过大门,朝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楼走去,那里又被称作‘快乐的跳蚤’。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门后,士兵瓦格纳开始对我大吼大叫,命令我继续工作,或者去‘医院’。没有人去了医院还能回来。我低下头,接着干活儿。
“那天剩余的时间我都紧盯着门口,晚上也没有睡觉。我第二天也在寻找再见到上校的机会。但我失败了。希姆莱一行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10月14日,索比堡的犹太人发动了起义。我事先也听闻了起义的消息,但那听起来相当不靠谱,我压根儿没有理会。他们反复商量,最后定下的方案居然是杀死几个士兵,然后一千来个犹太人发疯似的跑向大门。大多数起义者在头一分钟就被机关枪扫倒。疯狂的行动爆发时,我刚从车站干完活儿回来。押送我们的下士被冲在最前面的起义者打倒。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大家一起跑。我知道我的蓝色工作服会引来哨塔上乌克兰人的射击。但我躲到了大树背后,我身边的两个女人则中弹倒地。我在树下换上一个老人的灰色囚服。老人刚逃入森林的安全地带就被一发流弹夺走了性命。
“我想那天有大概两百人逃离了集中营。我们要么孤身一人,要么三五成群,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组织。获得自由后,筹划逃亡的人们无法保证大家的生存。大多数犹太人和苏联囚犯后来都被德国人追捕射杀,或者被波兰游击队发现后遇害。许多人在附近的农场中寻求庇护,但很快就被告发。一部分人在森林里活了下来,一部分人穿过布格河,去找向西推进的苏联红军。我很幸运。进入森林后的第三天,我被一个名叫奇尔的犹太游击队发现,他们的首领是一条英勇无畏的汉子,名叫耶切尔·格林斯潘。他将我带进游击队,命令队医照料我,使我恢复体重和健康。从上一年冬天起,我的脚第一次得到了适当的治疗。我同奇尔游击队在猫头鹰森林中游弋了五个月。我充当队医雅克兹克的助手,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有时甚至是德国人的性命。
“大逃亡后不久,纳粹就关闭了索比堡集中营。他们摧毁了牢房,撤走了焚化炉,将来不及烧掉的数千具尸体埋进大坑,在上面种上土豆。游击队庆祝犹太圣节的时候,德国国防军纷纷往西部和南部撤退,整个波兰陷入混乱之中。三月份,苏联红军解放了我们活动的区域。对我来说,战争结束了。
“我被苏联人扣押审讯了几个月。奇尔游击队的个别队员被送到苏联集中营,但我在五月份获释,回到了罗兹。但我已经无家可归。犹太人隔离区被夷为平地。我们位于城西的老房子也在战斗中被毁。
“1945年8月,我来到克拉科,骑自行车去默什叔叔家的农场。那里已经被另一家人——一个基督教家庭——占据。他们在战争期间从市政当局买下了农场。他们说他们对农场前主人的行踪一无所知。
“我离开农场,回到切姆诺。苏联人将那里列为禁区,我无法靠近。我在集中营附近露宿了五天,走遍了每一条土路和小径。最后,我找到了大会堂的废墟。它毁于炮弹轰炸,或是由撤退的德国人主动焚毁,只剩下倒塌的石料、烧焦的木材,还有孤零零的中央大烟囱。我没有找到大厅中的棋盘方格。
“在埋尸体的浅坑中,我发现了最近被挖掘的痕迹。那一带到处都是苏联烟头。我在当地小旅馆里问到此事,镇上居民坚称他们从未听说有人挖出了大坑中的尸体。他们还带着几分愠色说,这里的所有人都认为,就像德国人宣称的那样,切姆诺不过是个临时关押囚犯和政治犯的拘留营。我厌倦了露宿,本打算在小旅馆过夜,然后骑车返回南方,但竟然被拒绝了。他们不允许犹太人住店。第二天,我搭上去克拉科的火车,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
“1945年到1946年的冬天同1941年到1942年的冬天一样难挨。新政府正在组建,但最严峻的现实问题是食物短缺、燃油告急、黑市交易、大批难民回乡,以及苏联的占领。尤其是苏联的占领。数百年来,我们都在同俄国人打仗,曾经征服过他们,也曾经抵抗过他们的进攻,然后在他们的威胁下生活,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当作解放者一样欢迎。我们刚从德国人的噩梦中醒来,迎来的却是苏联解放的寒冷早晨。同我的祖国波兰一样,我疲惫、麻木,甚至对自己能幸存感到讶异。于是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生活上,努力再熬过一个冬天。
“1946年春天,我收到了堂姐丽贝卡寄来的一封信。她和她的美国丈夫住在特拉维夫。几个月来,她一直在写信、联系官员、给相关机构发电报,试图找到亲人的信息。她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才与我取得联络。
“我回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堂姐的电报,催促我去巴勒斯坦与她会合。她和丈夫戴维会电汇给我旅费。
“我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上,我们全家从不认为巴勒斯坦会成为一个犹太国家——但当我走下人满为患的土耳其货船,双脚站在后来被称作以色列的土地上时,我仿佛卸下了肩上的一副沉重枷锁。1939年9月8日至今,我第一次感觉到可以自由呼吸了。我承认,那天我激动地跪在地上,放声痛哭。
“也许我太天真了。几天之后,我抵达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发生了爆炸。那里是英军司令部的所在。后来我才知道,丽贝卡和她丈夫戴维都是哈伽拿【76】的积极分子。
“一年半后,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独立战争。尽管我曾有参加游击队的经历,但我在战场上的职责仍然是医生。我并不仇恨阿拉伯人。
“丽贝卡坚持让我继续读书。戴维那时已经成了一个备受尊重的美国公司的以色列经理,钱对他来说不成问题。然而,我在罗兹读书时并不用功,战争又让我有足足五年未接受教育,当我要重返教室时,已经是个二十三岁的男人,心灵饱受创伤,而且变得愤世嫉俗。
“不可思议的是,我学得很好。我1950年进入大学,三年后进入医学院。我在特拉维夫学习了两年,在伦敦学习了十五个月,在罗马学习了一年,然后又在苏黎世度过了一个阴雨连绵的春天。一有机会我就会回以色列,在戴维和丽贝卡夏天待的农场附近的居民点工作,同老朋友聊天叙旧。我已经亏欠我堂姐和堂姐夫太多,但丽贝卡说,作为艾希科尔家族拉斯基一脉的唯一幸存者,我获得再多的照顾都不过分。
“我选择了精神病学。在我看来,我之前所有的医科学习,都是在为我最终研究人类的精神做准备。我很快就对人类的暴力和支配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惊讶地发现,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有充足的数据可以解释狮群中的支配等级机制,有大量关于鸟类啄序【77】的研究,灵长类动物学家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描述我们近亲的社会组织中的支配与侵害行为,但关于人类暴力行为的机制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却鲜有人问津。很快我就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猜想。
“在我从事研究的这许多年里,我对上校进行了多方面调查。我对他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我知道他是三号特别行动队的军官。我见到他同希姆莱在一起。我记得老家伙临死前称他‘威利’。我联系了不同占领区的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红十字会、苏联人民法西斯战争罪法庭、犹太委员会,还有数不清的政府机构,但一无所获。五年后,我找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他们至少对我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但当时摩萨德还不像现在这样高效。何况,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人物要追查,比如艾希曼【78】、穆雷尔【79】和门格勒【80】。而只有我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向他们反映了上校的罪行,自然引不起他们的关注。1955年,我前往奥地利,同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会谈。
“维森塔尔的‘资料中心’位于维也纳贫民区的一座破烂建筑的底楼。那座建筑看起来就像被废弃的战时临时住宅。维森塔尔在那里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房间里全是塞满文件的柜子,而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地板空无一物。维森塔尔是个神经质的人,眼神中透露着不安。那双眼睛我总感觉似曾相识,起初我认为那是因为他是个狂人,后来我才想起,我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在镜子里无数次见过相同的一双眼睛。
“我的故事,我只给维森塔尔讲了个大概,说上校在切姆诺驱使囚犯供士兵取乐。当我提到后来我在索比堡再次见到上校,而上校成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随从时,维森塔尔竖起了耳朵。‘你确定?’他问。‘确定。’我说。
“尽管维森塔尔非常忙,但还是抽出了两天时间帮我追查上校。在他资料浩繁的文件库中,维森塔尔收藏有无数的文件、索引表和交叉索引表,包括两万两千多名党卫军士兵的姓名。我们搜索了特别行动队人事档案中的照片、军事院校的毕业照、新闻剪报,以及党卫军官方杂志《黑色军团》上的照片。搜索一天之后,我已经眼花缭乱了。那天晚上,我梦见一脸假笑的纳粹领袖向德国国防军军官授予勋章。但我们没有发现上校的线索。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终于在1942年11月23日的一张报纸照片上看出了蛛丝马迹。照片上是冯·布勒男爵,一位普鲁士贵族,一战英雄,战后在军中任将军。根据照片下的文字说明,冯·布勒将军在东线英勇反击苏联装甲师时牺牲了。我盯着泛黄的报纸上那张沟壑纵横的面庞看了许久。他就是老家伙。我将剪报放回文件夹,继续搜寻。
“我们到圣斯蒂芬大教堂旁的小餐馆吃完饭,维森塔尔忍不住感叹:‘要是知道上校姓什么就好了。如果知道他的姓,我肯定能把他揪出来。所有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军官的姓名都有记录。没有姓名就无从入手啊。’
“我耸肩道:‘我明天上午返回特拉维夫。’我们几乎查遍了维森塔尔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和东部战线的剪报,而我还有许多研究工作没有完成。
“‘不行!’维森塔尔厉声道,‘你是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切姆诺集中营和索比堡集中营的幸存者。你肯定能提供这些地方其他纳粹军官的信息。你至少应该下星期结束再走。我要采访你,并将采访记录下来。你提供的信息将异常宝贵。’
“‘不。’我说,‘我对其他军官不感兴趣。我只想找到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