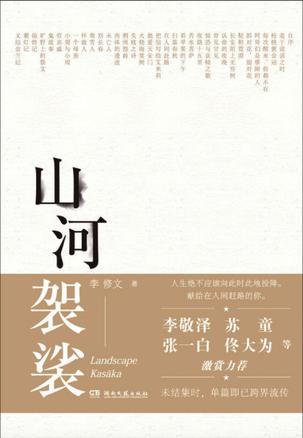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现在,只须闭上眼睛,我们全体动身赴默热弗前发生的事情的一些片断便重现在我的记忆中。奥什大街扎哈罗夫原先的公馆照得通亮的大窗户,怀尔德默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那些姓名,比如鲜红闪亮的鲁比罗萨7、灰白的奥列格·德·弗雷德,以及其他一些不可触知的细节——甚至包括怀尔德默沙哑的、几乎听不见的嗓音——引导我走出迷宫的正是所有这些东西。我的阿里阿德涅线。
头天傍晚,我正好待在奥什大街扎哈罗夫前公馆的二楼。人很多。和往常一样他们没脱大衣。我脱了。我穿过正厅,看见里面约有十五个人或站在电话机周围,或坐在皮椅上谈生意。我溜进一间小办公室,然后关上了门。我应当见的人已经在那儿了。他把我拉到房间一角,我们坐在两张扶手椅里,中间隔着一个矮桌。我把用报纸包好的金路易放在桌上。他立即递给我几沓钞票,我没有数便塞在衣兜里。我们一道离开办公室和大厅,那里人声鼎沸,穿着大衣的人们来来往往,气氛令人不安。在人行道上,他给了我有可能购买首饰的一位女子的地址,在马尔泽尔布广场那边。他建议我告诉她是他介绍我来的。天上飘着雪花,但我决定步行去。起初,我和德妮丝常走这条路。天气变了。下着雪,树木光秃秃的,楼房正面一片漆黑,我几乎认不出这条林荫大道了。沿蒙索公园的栅栏走,再也闻不到女真树的清香,只有湿土和腐叶的气味。
在被称作“花园广场”或“别墅”的一条死胡同的尽头,一栋楼的底层。她接待我的房间里没有陈设。只有我们坐的一张沙发和沙发上的电话机。女人四十开外,头发棕红,有些神经质。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她并不总去接,她接电话的时候,在一个小本上记下对方对她说的话。我把首饰拿给她看。我向她半价出让首饰别针和钻石手镯,条件是她立即付给我现钱。她接受了。
来到外面,当我朝库塞尔地铁站走去的时候,我想着几个月前到卡斯蒂耶旅馆我们房间里来的那个年轻人。他很快出售了一块蓝宝石和两枚首饰别针,亲切地建议和我分享利润。一位好心人。我向他透露了一点秘密,告诉他我们动身的计划,有时甚至阻止我出门的恐惧。他对我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古怪的时代。
后来,我去爱德华七世花园广场一栋楼二层的那套房间里找德妮丝,她的荷兰朋友凡·阿伦在里面开了一间女式服装店,正巧在“辛特拉”楼上。我记得这个细节,因为德妮丝和我常常光顾这间酒吧,它的厅堂设在地下室,可以不走正门,从另一扇门溜走。我想我认识巴黎所有有两个出口的公共场所和楼房。
这间极小的女式服装店里一片忙乱景象,和奥什大街一样,甚至气氛更加热烈。凡·阿伦正在准备他那套夏季时装,如此的努力,如此的乐观令我惊异,因为我怀疑是否还会有夏季。他正在一位棕发姑娘身上试一件料子轻薄的白色连衣裙,其他的时装模特儿在更衣室里出出进进。有几个人围着一张路易十五式样的写字台交谈,上面乱放着几张速写,几块衣料。德妮丝在客厅一角与一位五十开外的金发女子和一位棕色鬈发的年轻人谈话。我加入了他们的交谈。她和他将去蓝色海岸。人声嘈杂,谁也听不见对方的话。有人送上一杯杯香槟酒,不大清楚为了什么。
我和德妮丝挤出一条路,来到衣帽间。凡·阿伦陪着我们。我眼前又浮现出他那双十分明亮的眼睛和他的笑容,他把头伸出门缝,向我们送了一个飞吻,并祝我们好运。
我和德妮丝最后一次去康巴塞雷斯街。我们已经打好行李,一只手提箱和两个皮旅行袋在客厅尽头的大桌上等着。德妮丝关上百叶窗,拉好窗帘。她把缝纫机装进盒里,取下用大头针别在人体模型上半身的白布。我想着我们在此度过的夜晚。德妮丝照凡·阿伦给她的纸样裁剪或者缝衣服,我呢,我躺在长沙发上读一部回忆录或马斯克丛书中的一本侦探小说,她非常喜欢这类小说。这些夜晚是我享受暂时休息的唯一时刻,我可以幻想在宁静的世界里没有麻烦地生活的唯一时刻。
我打开手提箱,把鼓鼓囊囊地放在毛衣和衬衣内兜以及一双鞋的鞋底里的那几沓钞票塞进去。德妮丝在检查一只旅行袋,看看是否什么也没有忘记。我沿走廊一直走到卧室。我没有开灯,伫立于窗前。雪仍在下。在对面人行道上站岗的警察站在冬季来临几天前设立的一个岗亭内。从索塞广场又来了一名警察,他疾步朝岗亭走去。他与同事握手,递给他一个暖水瓶,两人轮流在平底大口杯里喝着。
德妮丝进来了。她来到我站立的窗前。她穿着毛皮大衣,身子紧紧贴着我。她身上有股胡椒的香味。在皮大衣里面她穿了件长袖衬衫。我们又躺到床上,床只剩下床绷了。
里昂火车站,盖·奥尔洛夫和弗雷迪在出站月台入口处等我们。他们身旁的一辆行李搬运车上堆放着为数不少的手提箱。盖·奥尔洛夫有只衣橱式旅行箱。弗雷迪正和搬运工讲价钱,并请他抽支烟。德妮丝和盖·奥尔洛夫同时讲着话,德妮丝问她弗雷迪租的木屋别墅是否容得下我们大家。火车站十分昏暗,只有我们所在的月台沐浴在一片黄色的灯光中。怀尔德默来与我们会合,他穿件驼毛大衣,大衣下摆像通常一样拍打着他的腿肚。一顶毡帽遮住他的前额。我们叫人把行李搬到各自的卧铺车厢,然后在外面,在车厢前等待开车的预报。盖·奥尔洛夫在乘同一辆火车的旅客中认出了一个人,但弗雷迪叫她不要和任何人讲话,不要引起别人注意。
我在德妮丝和盖·奥尔洛夫的包间里和她们一起待了一会儿。帘子放下了一半,我俯下身,透过车窗看见我们正穿过郊区。雪继续下着。我拥抱了德妮丝和盖·奥尔洛夫,回到自己的包间,弗雷迪已经安顿好了。不久怀尔德默来看我们。他的包间里暂时只有他一个人,他希望不再有人来,直至旅途终点。他的确担心被人认出来,因为几年前他在奥特依跑马场出了事故后,赛马报上多次登过他的照片。我们尽量劝他放宽心,对他说人们很快便忘记赛马骑师的面孔。
我和弗雷迪躺在铺位上。火车加速行驶。我们让小支光电灯亮着,弗雷迪烦躁地抽着烟。他为可能进行的检查有些惶惶不安。我也一样,但我尽量掩饰。弗雷迪·盖·奥尔洛夫、怀尔德默和我靠鲁比罗萨帮忙有了多米尼加的护照,但我们不能肯定护照真的有效。鲁比本人也对我讲过。我们的小命捏在一名更注意细枝末节的警察或查票员手里。只有德妮丝不冒任何风险。她是真正的法国人。
火车第一次停下。第戎。大雪减轻了高音喇叭的声音。我们听见有个人顺着过道走着。一间包房的门打开了。或许有人进了怀尔德默的包间。于是,我和弗雷迪神经质地狂笑不止。
火车在索恩河畔的夏隆市火车站停了半个小时。弗雷迪睡着了,我关了包间的灯。不知何故,我在黑暗中更觉得放心。
我试图想别的事,不侧耳倾听在过道里回响的脚步声。月台上,有些人在讲话,我抓住了他们的片言只语,他们大概待在我们窗前。其中一个人咳嗽着,带痰的咳嗽。另一个人轻声吹着口哨。驶过一列火车,有节奏的隆隆声盖住了他们的嗓音。
门突然开了,在过道的灯光中显现出一个穿大衣的人的身影。他用手电筒把包间从上到下扫了一遍,核对我们的人数。弗雷迪惊醒了。
“证件……”
我们把多米尼加的护照递给他。他漫不经心地审视了一遍,然后把护照交给他身旁的一个人。这个人被门扉挡住,我们看不见。我闭上了眼睛。他们交换了几句难以听清的话。
他朝包间内走了一步,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
“你们是外交官?”
“是的,”我不由自主地回答。
过了几秒钟,我想起鲁比罗萨给我们的是外交护照。
他一声不响地把护照还给我们,然后关上了门。
我们在黑暗中屏住呼吸。我们保持缄默,直至车开。它开动了。我听到弗雷迪在笑。他打开灯。
“去看看他们吧?”他对我说。
德妮丝和盖·奥尔洛夫的包间没有受检查。我们把她们叫醒。她们不明白我们为何如此心神不定。接着怀尔德默也来了,脸色凝重。他还在发抖。他出示护照时,人家也问他是不是外交官,他没敢回答,担心在便衣警察和检票员中间有位赛马爱好者把他认出来。
火车在白雪皑皑的景色中行驶。这景色多么悦目,多么友好。看到这些沉睡的房屋,我感到以前从未体验过的醉意和信心。
我们抵达萨朗什时天还黑着。一辆大客车和一辆黑色大轿车停在车站前。弗雷迪、怀尔德默和我拿手提箱,有两个男人负责搬盖·奥尔洛夫的衣橱式旅行箱。我们十来名旅客将乘大客车去默热弗,司机和两名搬运工把手提箱堆在汽车后部。这时一位金发男子朝盖·奥尔洛夫走来,正是头天她在里昂火车站注意到的那个人。他们用法语交谈了几句。后来她向我们解释说这是位远亲,一个俄国人,名叫基里尔。他指着那辆黑色大轿车,建议送我们去默热弗,驾驶座上有个人正等着。但弗雷迪谢绝了他的邀请,说他宁可乘大客车。
天上下着雪。大客车缓缓前行,黑色轿车超过了我们。我们正行驶在一条坡路上,每加速一次,大客车的车架子便颤个不停。我暗自思忖它会不会还不到默热弗便在路上抛锚。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夜色渐渐退去,升腾起一片棉絮似的白雾,枞树枝叶在雾中隐约可见,我想不会有任何人来这里找我们。我们没有任何风险。我们渐渐匿影藏形,连本来会引人注目的作客穿的衣服——怀尔德默的棕红色大衣和海军蓝毡帽,盖的豹皮大衣,弗雷迪的驼毛大衣、绿色长围巾和黑白二色的高尔夫大号球鞋——也消失在雾中了。谁知道呢?或许我们最终将化为乌有。或者变成车窗上蒙着的水汽,用手抹不掉的、久久不干的水汽。司机如何辨别方向?德妮丝睡着了,她的脑袋在我的肩头摇来晃去。
大客车停在广场中央,镇公所前。弗雷迪叫人把我们的行李搬到一架雪橇上,雪橇等在那儿,我们到教堂旁边的一家茶食店去喝点热的东西。茶食店刚开门,伺候我们吃喝的那位太太似乎很吃惊我们这么早就来光顾。也许使她吃惊的是盖·奥尔洛夫的口音和我们城里人的打扮?怀尔德默对一切都感到惊奇。他还没见过山,也没做过冬季运动。他额头贴着窗玻璃,大张着嘴,注视雪花飘落在死难者纪念碑和默热弗镇公所上,他问那位太太缆车如何运行,他是否可以在滑雪学校注册。
木屋别墅名为“南十字座”。它很大,用深色木材建造,百叶窗漆成绿色。我想这是弗雷迪向巴黎的一位朋友租来的。它俯瞰一条公路的一个弯道,从弯道看不见它,有一排枞树将它遮住。从公路沿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可抵达别墅。公路向前延伸,但我从来没有好奇地想知道它通向何方。我和德妮丝的房间在二楼,凭窗眺望枞树林上方,默热弗村尽收眼底。晴朗的日子,我锻炼目力,辨认教堂的钟楼,棕岩山山脚下一家旅馆构成的赭石色斑点,长途汽车站,以及最远处的溜冰场和公墓。弗雷迪和盖·奥尔洛夫的房间在底层,客厅旁边。要去怀尔德默的房间,必须再下一层楼,因为它位于地下,窗户如同船上的舷窗,与地面齐平。在那儿,用怀尔德默的话说,在“他的洞穴”里安身,是他本人的决定。
起初,我们不离开别墅。我们在客厅没完没了地打扑克。对这间屋子我记得比较清楚。一条羊毛地毯。一张皮长椅,上方有一个书架,一张矮桌。两扇窗户开向阳台。住在附近的一个女人负责去默热弗采购。德妮丝阅读在书架上找到的几本侦探小说。我也读。弗雷迪蓄了胡子,盖·奥尔洛夫每晚给我们做俄罗斯甜菜浓汤。怀尔德默要人按时去林子里取《巴黎体育报》,他躲在他的“洞穴”里读报。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打桥牌,他出现了,脸变了颜色,手里挥动着报纸。一位专栏作家追述近十年来赛马界发生的突出事件,其中提到“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怀尔德默在奥特依出的事故轰动一时”。文章配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怀尔德默的,比邮票还小。他为此慌了神,他怕在萨朗什火车站或在默热弗教堂旁的茶食店有人认出了他,怕为我们购买食品、捎带做些家务的那位太太认出他就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怀尔德默”。我们动身前一周,他不是在阿利斯康公园广场的家里接到过匿名电话吗?一个低沉的嗓音对他说:“喂!怀尔德默,一直在巴黎吗?”然后有人哈哈大笑,挂上了电话。
我们徒劳地一再对他说他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他是“多米尼加公民”,他表现得十分神经质。
有天夜里,早上三点钟光景,弗雷迪用力敲怀尔德默“洞穴”的门,一边大声嚷道:“我们知道你在里面,安德烈·怀尔德默……我们知道你是英国赛马骑师安德烈·怀尔德默……立即出来……”
怀尔德默一点不欣赏这个恶作剧,有两天不再和弗雷迪讲话。后来他们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