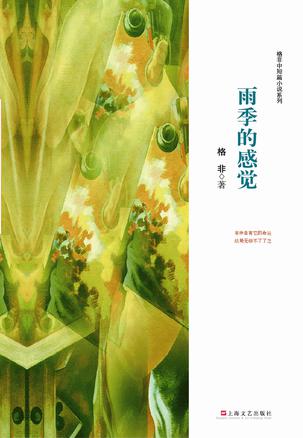哈代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克莱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一片晨光,颜色灰暗惨淡,神气鬼鬼祟祟,仿佛作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壁炉里只剩了一堆残灰;摆好了的饭桌上面,还放着满满两杯当时并没沾唇的葡萄酒,现在沫子也没了,颜色也浑了;她和他坐的椅子都空着;其余的家具,也都带着它们那种老是无可奈何的神气,不管人烦不烦,一死儿地追问怎么个办法。楼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但是待了不到几分钟,却有人敲门。克莱想,来的人大概是住在小房儿里伺候他们那个女街坊。
那时候,克莱已经穿好了衣服了。他听见女仆来了,就心里琢磨,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家里有外人,一定很不方便,因此就开开窗户,对那个女人说,他们那天早晨自己就可以安排一切,不用她在这儿伺候。她手里拿的那一罐儿牛奶,就放在门外头好啦。他把那个女人打发走了以后,就在房子后面,找到了些木柴,很快就把火生起来了。伙食房里有的是鸡蛋。黄油。面包和别的食物,他在牛奶厂里,又学得很会作些家务事,所以一会儿就把早饭作好了。壁炉里的木柴哔剥地响,烟囱上的烟气滚滚地冒,老远看来,好象柱头上雕着莲花的柱子;本地人打那儿过的,见了这种情况,都不由想到这一对新婚夫妇,都不觉羡慕他们新婚的快乐。
安玑把屋里的一切,最后又看了一眼,跟着走到楼梯下口那儿,用一种合于常例的声音说: "早饭作好啦!"他开开前门,在晨间清新的空气里闲走了几步。待了不大会儿,他就回了屋里,那时候,苔丝已经在起坐间里了,正死板板地把杯盘等等重新安排。既是她那时已经穿得整整齐齐的了,而他叫她的时候,离那时又不过两三分钟,那么,他叫她的时候,她一定是早就穿戴好了的了,或者差不多穿戴好了的了。她把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大圆髻,身上穿了一件新连衣裙,一件浅蓝色的毛料衣裳,领子上镶着白绉边儿。她的脸和手仿佛冰凉,也许是她起来,穿着衣服,在冷屋子里坐了许久了。克莱刚才叫她的口气,显然非常温文有礼,她当时听了,心里不由得一时重新生出一线的希望来。但是现在她一看他的神气,那点儿希望就又消逝了。
说句实话,从前他们两个好象一盆烈火,现在他们却只是一堆残灰了。昨天晚上是热辣辣的一片愁绪,今天早晨却是闷沉沉的满怀抑郁了。仿佛没有东西,能把他们的情感再鼓动起来,能使他们的感觉再跟从前一样地热烈。
他对她说话的态度老是温和的,她回答他也老是同样地喜怒不形于色。等到后来,她才走到他面前,往他那副眉目清晰的脸面上瞅着,仿佛并不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有形可见的活东西似的。
"安玑!"她说,说了这一声,又停住了,用手轻轻去触他,轻得好象微风一样,仿佛她不大能够相信,这就是她那位旧日情人的肉体。她的眼睛仍旧水汪汪的,她那灰白的两颊仍旧象旧日那样丰润饱满,不过半干的眼泪却在那儿留下了痕迹了;她那鲜润红艳的嘴唇儿,也变得跟她的两颊差不多一样地灰白了。固然不错,她的心房仍旧跳动,她仍旧还活着,但是她心里的悲痛,却重重地压在她身上,把她的生气压得时断时续,如果稍微再增加一点儿压力,她就一定要真病倒了,一定要两眼无神,一定要嘴唇儿变薄了。
她的样子是绝对纯洁的。这是老天成心耍离奇古怪的把戏,才在她的容貌上给她印了一副女儿无瑕的标志,让他傻了一般地瞧着她。
"苔丝!你得说你说的都是瞎话!一定是,一定是瞎话!" "不是瞎话!""字字是实?""字字是实。"他带着哀求的神气瞧着她,仿佛他情愿听她亲口说一句谎话,纵然明明知道是谎话,也情愿用诡辩的方法欺骗自己,把谎话当作真话。但是她只回答说,"不是瞎话。""他还活着吗?"于是安玑问。
"孩子死啦。"
"那个男人哪?"
"还活着。"
克莱脸上显出一种最后绝望的神气来。
"他在英国吗?"
"是。"
他来回瞎走了几步。
"我的地位,是这么一种情况,"他突然说。"我总想,无论谁都要这么想,我不娶有身份。有财产。通达世务的女人,我把那种野心一概放弃了,那我就不但可以得到一个天然美丽的女人,也一定可以得到一个质朴纯洁的女人了;谁知道,唉,也罢,我不配说你的不是,我也不愿意说你的不是。"苔丝对于他的地位完全了解,所以那句话的下文用不着说出来。这件事叫人最感痛苦的地方,就在这儿了。她可以看出来,他是面面都吃了亏的了。
"安玑,我当初所以答应你跟我结婚,因为我知道,闹到究竟,有最后让你脱身的办法;固然我倒是希望,你永远也不," 她的嗓音都哑了。
"最后的办法?"
"我是说,最后跟我脱离关系的办法。你可以跟我脱离关系呀。" "什么办法哪?""跟我离婚哪。""哎呀天哪,你怎么就这样简单!我怎么能跟你离婚哪?""不能吗,我把话都告诉你了,还不能吗?我原先认为,我的自白,很够构成离婚的理由的了。""唉,苔丝,你太,太,幼稚了,太没有知识了,太粗鲁浅薄了,我想!我简直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你不懂得法律,你不懂得!""那么,你不能跟我离婚了?" "实在不能嘛。"苔丝满脸的惭愧,立时和她原来满脸的苦恼混合。
"我本来想,我本来想,"她打着喳喳儿说。"唉呀,现在我才明白,在你看来,我多么坏了!不过请你相信我,请你相信我,我对天起誓,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你会不能跟我离婚!我倒是希望,你别那么办来着;不过我可实实在在地相信,只要你一拿定了主意,只要你一不,不,爱我,你就可以把我甩开!" "那你是想错了,"他说。
"哦,这么说起来,我应该把那件事办了,昨天晚上,就应该把那件事办了!可是我又没有那样的胆量。唉,我个人就是这样!" "干什么的胆量?"因为她没回答,所以他就拉住了她的手问她,"你想要干什么来着?""想要自尽来着。""多会儿?"他这么一追问,她畏缩起来。"昨儿晚上,"她回答说。
"在哪儿?"
"在你挂的那一串寄生草下面。""哎呀!用什么法子?"他严厉地问。
"你要是不生我的气,我就告诉你!"她一面畏缩,一面回答说。"我本来想用捆箱子的绳子来着。可是到了最后一步,我又没有胆量了!我恐怕我真那么一来,别人就都要说你的坏话,于你的名誉就有了妨害了。"这段供词,原是逼出来的,并不是她自动地说出来的;供词里让人想不到的情况,显然使克莱震惊。但是他仍旧拉着她的手,同时把眼光从她脸上移开,低垂下去,说,"你现在听着,我决不许你再想那种可怕的事!你怎么能那么想哪!我是你的丈夫,你得答应我不再想那种事。""我愿意答应你。我早就看出来,那种办法非常地坏了。""坏!你那种想法没出息到家了。""不过,安玑,"她辩护说,同时一点儿也不在乎地把眼睛睁大了,安安静静地看着他,"我想那种办法的时候,完全是为了你起见,完全是想要让你跟我脱离,可又下落离婚的骂名。要是为我自己,我作梦也想不到那个呀。话又说回来啦,我死在我自己手里,究竟还是太便宜了。我应该死在你手里才对,因为我把你毁了么。既然你没有其它脱身的办法,那么,你要是能把我置之死地,我想,我一定要爱你爱得更厉害,这是说,如果我爱你还能更厉害的话。我觉得,我一点儿价值都没有!我觉得,我是你一个大大的绊脚石!" "别说啦!""好吧,你不让我那样,我就不那样好啦。我决不跟你翻着。"他知道这是实话。昨天晚上,她不顾一切闹了一阵之后,现在一丁点儿劲头儿也没有了,不用再怕她有什么孤注一掷的举动了。
苔丝又去安排早饭,好占着身子。她这样作,多少有些成功。安排了一会,他们两个就都在桌子的一面儿坐下,免得彼此的眼光相碰。起初两个人互相听见彼此吃喝的声音,觉得有点儿别扭,不过这是没法子的事;好在他们两个吃的东西不多。吃完了早饭,克莱站起来,告诉苔丝什么时候回来吃午饭,就往水磨厂,呆呆板板地去实行他那研究水磨的计划去了,因为那是他到这儿来唯一的实际原因。
他走了以后,苔丝站在窗前,顷刻之间,就看见他跨过那座通到水磨磨坊的大石桥。他下了桥,又往前走去,穿过一道铁路,就再看不见了。于是,苔丝连气都没叹,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房子里,动手清理饭桌,归置屋子里的东西。
打杂儿的女仆一会儿就来了。苔丝起初觉得有她在面前,很不得劲儿,不过后来又觉得有她在面前,可以减少烦闷。到了十二点半钟的时候,她就离了厨房,叫女仆一个人在那儿预备一切,自己回到起坐间里,坐在窗前面,老远看着,等克莱再在石桥后面出现。
靠近一点钟的时候,果然看见克莱来了。虽然还隔四分之一英里,而苔丝远远看见了他,却不觉脸上又红又热。她跑到厨房里,吩咐他一进门就把饭开好。他回来的时候,先到昨天他们一块儿洗手那个屋子里去了一趟,他刚一进了起坐间里,桌子上的盘子也同时揭开了盖儿,仿佛是盘子盖儿揭开,是由于他的动作似的。
"真准!"他说。
"不错,我瞧见你过桥来着,"她说。
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只谈了些极平常的闲话,说他一早晨在水磨磨坊里作的事情,说磨房里分离麦糠的方法和老式的机器他说,恐怕这种机器,不大能在近代改良的新方法方面对他有什么启发;有的机器,好象还是当年这个水磨给隔壁寺院里那些僧侣磨面的时候用的哪,现在那座寺院早已成了一片瓦砾了。中饭吃完了,不到一个钟头,他又出门儿去了,到了黄昏的时候,才回到家里,一晚上净忙于文件上。她恐怕她在面前碍手碍脚,所以那个老婆走了以后,她就上了厨房,在那儿尽力地忙了足足有一个多钟头的工夫。
克莱来到厨房的门口那儿说,
"你别这么死气白赖地作活儿啦,你是我的太太,并不是我的仆人哪。"她抬头看去,神色开朗了一点儿。"我可以把自己当你的太太看待吗?"她用可怜的口气自嘲自讽地嘟哝着说。"你说的是名义上的太太吧!好吧,那也够了,我也不希望别的。""你可以把自己当我的太太看待,苔丝!你本来就是我的太太么。你刚才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清楚,"她急忙说,说的时候,字音里都含着泪。"我只觉得我,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不体面。我从前早就告诉过你了,说我不够体面的,因为那样,所以我不愿嫁你,可是,可是你偏来逼我!"她一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跟着就把脸背了过去。别的人,无论谁,看见这种样子,大概都要回心转意的,只有克莱不成。他平时虽然温柔多情,但是在他内心的深处,却有一种冷酷坚定的主见,仿佛一片柔软的土壤,里面却藏着一道金属的矿脉,无论什么东西,想要在那儿穿过去,都非把锋刃摧折了不可。他不赞成教会,就是由于这种障碍;他不能优容苔丝,也是由于这种障碍。并且,他的情爱里真火少,虚光多;他对于女性,一旦不再信仰,就马上不再追求;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容易受感动的人,完全相反,因为那种人,理智方面,纵然觉得一个女人可鄙,情感方面,却还是迷恋不舍。当时克莱在一旁等候,一直等到苔丝哭够了的时候。
"我倒愿意,英国的女人,有一半能象你这么体面哪,"他对于一般女人,忽然发了一阵牢骚,说。"这不是什么体面不体面的问题。这是有关原则性的问题!"他对苔丝说了这些话,还说了些性质相近的话,因为,他当时的心情,仍旧在反感浪头的冲荡之下;本来一个直率人,一旦发现自己因为只看外表而上了当,那他就必然要起反感,就必然要反爱为憎。固然,在他这种心情之中,还潜伏着一种同情心,一个通达人情世故的女人,很可以利用这一点,使他回心转意。但是苔丝却没想到这一点;她觉得,一切加到她身上的,都是她应当受的,所以她几乎连口都不开。她对他的忠心那样坚定,真几乎可以说令人可怜;她虽然天生脾气急躁,但是她决没有因为他说的话(不论说的什么),而露出不应当有的态度;她完全不顾自己;他招她,她不恼(暗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他无论怎么样待她,她都一点儿也不往坏的方面想。现在很可以说,她就是耶稣的门徒所教的那种(耶稣的门徒圣保罗等宣抚爱,见《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等处。)爱的化身,又回到这种自私自利的现代世界里来了。
他们两个这一天,由黄昏到黑夜,由黑夜到天明,都过得跟头一天一点儿不差。有一次,只有一次,她,也就是从前那个自由。独立的苔丝,曾冒昧地对他作过表示。那正是他第三次吃完了饭要起身到水磨磨坊里去那一回。他从桌子旁边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对她说了一声"再见";她也回答了一声"再见",同时把嘴微微掉到他那一面儿。但是他却没接受她的好意,只急忙转过身去,嘴里说,"我一准按时回来。"苔丝仿佛挨了打似的,立时缩成了一团。从前的时候,他老扭着苔丝的意思,强要跟她的嘴接触,他老欢欢喜喜地说,她的嘴唇。她的气息,跟她吃的黄油。蜂蜜。牛奶。鸡蛋一样的味道;他亲了她的嘴唇,就可以从那儿得到滋养;他以前老说这一类疯疯癫癫的话。但是现在呢,他对于她的嘴唇。气息,却完全不理会了。他看见了她忽然退缩的样子,就对她温和地说,"你要晓得,我一定得想个办法。咱们现在自然非在一块儿住几天不可,免得立刻分开了,让人家说你许多坏话。不过你要明白,这不过是顾全面子的办法就是了。" "是,"苔丝出着神儿说。
他出了门,往水磨磨坊去了,在路上曾站住了一下,有一会儿的工夫,后悔刚才没对她温柔一些,没至少吻她一次。
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过了这一两天的愁闷日子;倒是不错,他们住在一所房子里;然而可比他们还不是情人那时候更疏远了。她看得很清楚,他真象他自己说的那样,正在瘫痪了的活动之中生活,在没有办法之中硬要想办法。她真没想到,他外面儿那么温柔,骨子里会那么坚定,所以她看到这一层,就吓得不知所以了。他这种一贯到底的决心,真太残酷了。她现在不再希望他会饶恕她了。他在水磨磨坊的时候,她曾有过一两次,想要悄悄地自己离开这儿;但是又一想,这种办法,要是传到外面,不但对他没有好处,反倒会是他的障碍,会使他丢尽脸面,因此也就罢了。
同时,克莱正在那儿琢磨,一点儿不错,正在那儿琢磨。他就没有一时一刻不琢磨的。他琢磨得什么都不顾了,琢磨得人都瘦了,琢磨得他从前喜欢家庭生活的天机生趣也完全折磨干净了。他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怎么办哪?怎么办哪?"他念明的话,偶然让她听见了。于是她就把以前那种不谈将来的缄默打破了,开口说,"我想,你大概不预备跟我,长久同居了,安玑,是不是?"她问,问的时候,脸上很安静,但是她那两个嘴角使劲往下聋拉的情况,却可以使人看出来,她脸上忍疼自励的安静,完全是机械地作出来的。
"我不能跟你同居,因为我要是跟你同居,我就不免要瞧不起我自己,也许还要瞧不起你哪,那就更糟了。我这自然是说,我不能象普通的了解那样,跟你同居。现在,不管我觉得怎么样,反正我并没瞧不起你。我打开窗子说亮话好啦,不然的话,我恐怕你不明白我所有的困难。既然那个人还活着,那咱们怎么能同居哪?你的丈夫本来应该是他,并不是我。要是他死了,这个问题也许就不一样了,而且,困难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层,还有一方面,也得加以考虑,那就是说,这件事还关系到别人的前途,不止关系到咱们俩。你得想一想,过了几年以后,咱们生下了儿女,这件事传了出去的情况,,因为这种事儿,没有不传出去的。就是天涯海角,也免不了有人来。有人去。到了那时候,你想,咱们的儿女老让人家耻笑,他们一天大似一天,心里也一天明白似一天,那他们该多苦恼!他们明白了以后,该多难堪!他们的前途该多黑暗!你要是琢磨琢磨这种情况,那你凭良心说,还能再要求我跟你同居吗?你想咱们受眼前的罪,不强似找别的罪受吗?"(引用《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一场第八十行。)苔丝的眼皮本来就愁得往下奇拉着,现在仍旧往下聋拉着。
"我不能要求跟你同居,"她回答说。"当然不能;我以先还没想得这么远哪。"我们老实说,苔丝到底是个女人,她希望重圆的心非常地强烈,所以竟暗自琢磨,和他亲密地一室同居,日久天长,也许能使他那冷酷的理性,化为温暖的柔情。她虽然象平常说的那样,率真纯朴,她却并不是智力发育不全。要是她不曾本能地知道耳鬓厮磨的力量(比较哈代一八八九年七月九日的日记:"爱情依耳鬓厮磨而生,但是贴实接触则死。"),那我们只好说,她没有作女人的资格了。她看得清清楚楚,要是这种办法再没有效果,那么,别的办法就更没有用处了。她固然对自己说过,用计谋。使手段,希望使情况好转,是不应该的,但是前面说的那种希望,她却没法消灭。现在克莱已经表示了他最后的意见了,这种意见,她已经说过,是她从前没想得到的。她实在没顾虑得那么远,也没打算得那么周密;他描绘的那幅清晰画图,说她可能有儿女,将来会瞧不起她,那一番话,让她那样一个心地忠厚的人听来,真觉得入情入理,因为她那颗心,自来就是慈爱的。作一个好人固然不错,但是她以往的经验使她明白,在某些情况之下,如果能够免得作人,比作一个好人还好。她跟一切受过折磨而有先见的人一样,听了"你要下世为人"这句命令(象庶利。蒲吕东(庶利。蒲吕东(1839—1907),法国诗人兼批评家,著有《孤寂》。《命运》。《幸运》等。此处所说待考。)说的),就象听了宣读判决书一样,尤其是,如果这句命令,是对她未来的儿女发出来的。
然而"自然夫人"总是阴险狡狯,难以捉摸,竟使苔丝,顶到现在,因为爱克莱的缘故,一时糊涂,忘了他们同居,可以产生新生命,可以把她自己叹为不幸的痛苦,强加到别人身上。
因此她就觉得,他那番道理,无法驳辩。但是克莱自己心中,却想起了一种驳辩之辞,因为神经过敏的人,天生都有一种跟自己争论的脾气;他几乎害怕,苔丝会真拿那种话来和他驳辩。克莱这种想法,原是根据了苔丝与人不同的体质,苔丝如果利用这一点,也许很有达到目的的可能。并且她还可以说,"咱们到了澳洲的高原上,或者得克萨斯州(美国之一州,在美国南部。)的平原上,谁还知道我有什么不幸,谁还来管我有什么不幸,谁还来责备我,谁还来责备你哪?"然而苔丝却跟大多数的妇女一样,把一时心里所想到的看法,认为是永远不能变更的事实。她也许不错。因为,一个女人的直觉,不但使她感到自己的辛酸,并且使她感到她丈夫的辛酸(原文由《旧约 箴言》第十四章第十节,"心中的苦楚 自己知道"而来。);责备她丈夫或者他的子女那种话,即便不会由生人的嘴里说出来,而丈夫自己那种吹毛求疵的脑子,责备自己的话,他自己的耳朵总是听得见的呀。
他们两个,同室异心,已经三天了。也许有人可以冒昧地说这样一句似非而是的怪话:他的兽性如果更强烈,那他的人格就会更高尚。我们并不这样说。不过,克莱的爱,却的确可以说轻灵得太过分了,空想得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了。对于这种人,在他们跟前,有时反倒不如不在他们跟前,能更感动他们。因为所爱的人,不在他们跟前,他们可以把他们所爱的人想象一番,在这种想象里,反倒能把所爱的人实在的缺点消灭。她看出来,她的形体不象她所预料的那么有力量。那么能感动他。先前那个比喻的说法是对的了:她是另外一个女人了,不是原先激起他的爱欲那一个了。
"我把你说的话,都琢磨过了,"苔丝说,同时把一只手的食指,在桌布上划着,用带着戒指的那一只支着前额,戒指仿佛嘲笑他们两个似的。"你说的那些话,没有一句不对的;是不能那么办,你是得离开我。" "不过你哪,你怎么办哪?""我可以回娘家呀。"克莱却还没想到这步办法。
"一定可以吗?"他追问说。
"一定可以。咱们既是非分离不可,那咱们早早分离完事,不更好吗?你从前说过,男人在我面前,极容易把持不住;要是我老跟你在一块儿,也许你会把持不住,忘了你的理性,忘了你的愿望;如果真有那一步,那以后你的后悔。我的烦恼,还能让人受得了吗?" "你可愿意回娘家?"他问。
"我要跟你分离,所以我要回娘家。" "那么,就那么办吧。"苔丝听了这句话,虽然没抬头去看克莱,却不觉失惊一动。因为提出办法是一回事,允诺实行又是一回事,这一层只怕她明白得太快了。
"我早就害怕要有这一步了,"她嘟哝着说,脸上驯驯伏伏地不动声色。"我并不抱怨,安玑。我,我觉得,这是顶好的办法。你对我说的那些话,我听着真是至情至理。因为,比方咱们两个同居,虽然不会有外人来揭我的短处,但是以后日子久了,可保不住你不为一点小事儿闹脾气,保不住你不把我从前的事儿顺口说了出来,也就保不住别人听不见,也许还让咱们的儿女听见哪。现在这种样子,不过让我伤心罢了,到了那个时候,那可就要叫我受大罪,就要要了我的命了。所以我现在离开你,是顶对的。我,明天就走。""我也不在这儿住啦。我不过不肯先开口就是了,其实我早就觉得咱们应该分居了,至少得分居一些日子,等到我能把事情的真相看得再清楚一些,可以给你写信的时候。"苔丝偷偷地看了她丈夫一眼。只见他满脸灰白,甚至于还全身颤抖。但是苔丝看到,她嫁的这个丈夫,外面上那样温柔,心里头却那样坚定;看到他有那种意志,一定要把粗鄙的感情,化为精妙的感情,把有形的实体,化为无形的想象,把肉欲化为性灵,她仍旧跟从前一样心惊胆寒。他那种支配一切的想象,仿佛是狂暴的风,一切本性。倾向。习惯,遇到了它,都要象枯萎的树叶一样。
他大概看见她偷偷地瞧他来着,因为他接着解释说,"凡是跟我不在一块儿的人,我想起他们来,都觉得比在一块儿的时候可爱。"于是又带着玩世不恭的态度,加了一句说,"谁知道哪,保不定咱们两个,将来有那么一天,都过腻了,就又凑到一块儿,和好起来了;这样的人可就太多啦。"克莱当天就动手捆扎行装,苔丝也上了楼,去收拾东西。他们这两个人,对于任何象是后会难再的离别,都觉得非常痛苦,所以他们如今预备分手,却假装着后会有期,作种种猜想,宽慰自己;但是两个人心里,却分明觉到,明天这番别离,也许就是永远的别离。他知道,她也知道,刚一分手的头几天,他们互相牵引的力量,在她那方面,这种力量是不凭借才艺的,大概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强烈,但是日久天长,这种力量自然要淡下去的;既是现在,克莱根据实际上的情况,认为不能跟她同居,那么,分离了以后,头脑更清楚,眼光更冷静,不能同居的理由,也许该更明显了。并且,两个人一旦分离,不再在共同的居室和共同的环境里,那就要有新的事物,不知不觉地生长出来,把空下来的地方填补起来,意外的事故,就要阻碍了旧有的打算,往日的计划,也就要让人忘记了。